
我突然很想上贴一则旧文,它完成于2001年的秋天。2007年的夏天,我重返拉萨。如果说初读这个雪域圣城我是用文字记下了自己的感悟,那么时隔六年之后的再读,我则用图片去诠释。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对比,也是一种纯个人视角的原始纪录:纪录下的,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圣城拉萨的日新月异……
信步拉萨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随意走走,无人相识也无人等候,由着性子像孤魂野鬼似地东瞧瞧西望望。你会感觉如何?
如果这个城市又是一个容人亲近的小城,小得没有板起面孔的高楼大厦,无法去哪儿“朝花”都不必“夕拾”,风情点点圣迹处处就搁在路边,甚至让人撩不开大步,只消碎碎地转悠着溜达。直到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铺里,一边听着“香帕拉并不遥远”的弹唱,一边嚼着“青椒炒肉丝”,是不是一种自在的大快意?
如果这个小城又偏偏是坐落在海拔3600以上的高原古城和圣城,虽然伸手还抚摸不到蓝云与白云,但是却可以触摸到神佛与历史。“煨桑”的柏枝燃起的青青烟霭,缭绕着寺院的金顶。街头横幅一样的风马旗在洒落着六字真言和甘珠尔…….。
如果说它还绝对的千姿百态,街头流动的,绝不是步履匆匆见惯司空的人群,而是着红色僧袍的喇嘛,一头绿杉石孔雀石链饰的康巴女人,永远摇着轻径筒的老妪和叩着长头的孩子,一脸庄严木然的朝圣进香的乞丐,还有那么多,多到了一个联合国似的,然而却把优越和自大丢在了老家的老外……。
感觉真好!信步拉萨,的确无须去找感觉了,也许倒是需要寻找自己。因为太多太厚太神秘太自在的感觉弥漫全城,直涌过来淹没了自我。不过几天就会发现自己在变,心在变得透明,人在变得普通,情也变得神圣,变得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两只脚,差不多已经面目全非,自己不认识自己了。
其实,在拉萨,“自己”这破玩艺儿不要也罢!有两只脚一双眼也就足够了。当然,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只是因为加上了一只镜头。
在拉萨的日子里,我们就以这副模样步态散漫地穿行在街头。清凉如水的阳光不过两三天就让我们一脸红黑,虽不致被人错认为是“巴桑”或“仁措”,但我腆着肚子最先变成“援藏干部”,在圆头大脸上涂抹防晒霜的小喻几被认成“活佛”,凯哥戴了墨镜然而更糟——单单晒黑了鼻子!只有文斗,依旧一个潇洒的三湘哥儿,晃晃悠悠地走在拉萨。
当然庆幸在短暂的人生中,有这样闲适的时光属于高原,属于拉萨。让我们在信步中细品,在随意中参悟。、
啊,我的拉萨,我的天堂。
二
“回到拉萨,回到拉萨”,有时候,我们风尘仆仆赶着落日往回走。天荒地老的旷野中,本来好像是无牵无挂,但走近拉萨,才知道我们是那样急迫地要扔下一途的沉重,无助和情思,要回到拉萨的“家”。
“家”在哪里呢?一千三百年前一个称为“卧塘”泥沼地的边缘,即如今大昭寺北,一条以藏式居民建筑为主的北京东路上,一间叫做“吉日”的客栈。
“吉日”是一个与星级毫不沾边的热闹的“大杂院 ”。二层骑楼的门洞里,有一个宽敞的大院落。它的招牌破旧得毫不起眼,让人注目的倒是那个骇人的“疯牛餐厅”。
在整个西方谈牛色变的日子里,“疯牛餐厅”却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们。那是一座位于大院正中的方形藏式小楼,它的二楼是一个安静到有几分冷落的藏茶楼,而一楼却是一个永远都挤满了摆动刀叉大啖牦牛肉的碧眼金发们。
在小楼的四周尤其是东侧,则是三层简易却风味十足的客房。一溜走廊上,总有些冷眼看喧嚣的漂泊者。远足归来,扔下行囊,我们也常扶着栏杆,欣赏那小楼攀满花蔓的窗扉里,飘出热烈的弦音鼓声和又高又飘的女声齐唱。每天傍晚,这里总是有一个从来无须排练的游方民间的藏族艺术团,在小楼后一块洗衣和通过公共浴室的角落里,匆忙地更换各式戏袍,再钻进楼内。那精致的黑牦牛的披挂,绝不是一个“画了条纹的布袋”,即
我们通常住在三楼,虽然只有公共卫生间,但低廉到30元一天的房费,却拥有一个宽大的房间和一只宽大的床,且有彩电。最让人快意的是免费洗衣,一个白布袋塞进所有泥尘汗渍的衣衫放在门口的长椅上,傍晚则收获一袋迭好的干净的衣服。这总使我想起了《洗衣歌》中那些藏族姑娘们调戏解放军的纯净欢乐。而且就在这一排长椅上,形成了漂泊者交流扎堆儿的沙龙。高原上各地路况、气象、拍摄点乃至心曲、心得、感受之类,在这里往往能第一次加以整理和倾述。还有不少人在阅读和笔记,长椅上又添了几份温馨和恬静。
小院里是起点也是终点,俯视下去,各式汽车往往带来一些繁杂,一些伤感和一些讳言莫测的故事。有时,在越野吉普中间,还挤进一辆从尼泊尔闯来的“大奔”。我见过一辆巨大的奔驰大卡车,这个大家伙的货箱已被改成带顶蓬,又带箱式板床的大阁楼,显得又神秘又舒适。引起了为我们开车的边巴次仁极大的兴趣。
边巴开的是一辆饱经折腾的丰田62,那是一辆跑着跑着不知什么时候就“哐当”一声掉下点零件的老爷车。即使如此,在开往中尼边境,一个可以看到希夏邦马峰的山口上,为抄近路,边巴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居然驾着车冲出公路,一头扎下山坡,在那车内已望不到前方地面的坡度中俯冲而下。而回到吉日,他在“大奔”那儿转悠着打什么主意呢?
在各家有“驴坛”的网站上,吉日大门口的招贴栏很有名气。那是一个活跃的极具可读性的网络版“刊物”。在拉萨的日子里,我常常有事没事在那里瞎读一气。有招募游兵散勇的;有求旅伴而可读成求侣伴的;MM们用娟秀的字体温存的语气,报告哪里有山崩桥断;还有热心肠的图文并茂的路线攻略和租车的招标;日文和英文中似乎有不少惊叹和无奈……。在这个招贴栏上,现代信息社会的隔膜冷酷,被求助、扎堆儿的温情所取代。一种不可知的旅途,的确拴着了一群素不相识来到雪域高原上乱蹦的蚂蚱!
走出吉日的门洞,也就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没有人会认识你,没有人有兴趣对你说三道四,完全不要指望你精心地扮酷扮靓会引起围观或注目。我曾见到过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却自称是“广佬”的哥儿,这个染了黄发的“新新人类”,把两只巨大的鹰翎,斜斜地插在一辆山地车的把手上,黑色的背心,黑色的怪异墨镜和黑色的羊皮护手,外加一大串念珠挂着,还有八个或十六个口袋的牛仔裤。装配了如此的行头招摇过市,骑行在几个红衣喇嘛走过大街上,除了我听到有人吐出“傻B”二字外,连一缕倾情的顾盼也没有赚到。
门外的拉萨,就是这样一个见怪不怪处惊不变的小城。出了吉日,往西去不远处有一个十字路路口,左拐走向大昭寺,右拐则走向小昭寺。也许就是因为那里千年以来升起的淡蓝色烟霭,稳沉地覆盖着、涵养着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山川大地,不动声色地淹没了所有外来的惊扰和催促。只把吉日,只把这样的一些客栈内的院落,留给了远方的客人。
三
在一个傍晚,我推动着铜质大经简走出了小昭寺那阴暗的回廊。门外,光鉴照人的青石板上,有几个叩着长头的女人匍匐在地。
此时,一个身材修长面容姣好的高贵少妇跳进眼帘。与那几位衣衫褴缕、头发花白、脸上一道道深槽般皱纹的老妪比较,说她是“高贵”的,是说她是那么年青,腰枝是那么纤细,“邦典”裙片是那么鲜艳,甚至她的眼睛里还闪动着光泽。她从她们中间弓起腰来,竟如藏族舞蹈中的少女那样,在暗色的背景中拉出了一条抬头塌腰的优美曲线,定格片刻,却又同样地双手前伸,俯卧在地,眼中的那片光泽不见了,仿佛已飘进寺中,飘进了虚空。
我站住了,我突然注意到,在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年青的藏簇男人。他只是坐在青石板地上,把一只热水瓶中冒着热气的奶茶,倒进了粘粑碗中。他不时有些敌意的看着我手中的像机,不时又是那样深情地注视着那人群中执着地一起一伏的年青女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朝圣者呢?
她为什么不去大昭寺而到这有几分冷清的小昭寺呢?她年轻的生命,又有怎样的祈求要倾述给菩萨呢?作为一个信步拉萨的外来者,每一次我面对着叩长头这道独特风景,都感到心灵在强烈的震撼中,使我绝对不能熟视无睹的是那些更加年轻的孩子们。
在大昭寺那一长排重叠着永远跳动着火苗的灯台下,我曾见到过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他的身边没有父母、没有老人,他是那么小,当那瘦弱的身驱仆倒在地的时候,他仿佛已经消失。只有当他抬起头来,才能见到那黑乎乎的小脸上有一双专注纯净的眼睛。他的小手中套上了一付脏兮兮的牛皮护套,腰上还别了一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孩子,他是谁?他又为了什么呢?
从老人到孩子,叩长头的人群连贯着没有断层。然而,没有人能读懂他们的心结和途中的故事。也没有人视拉萨的乞讨者为盲流,远至青海、四川、滇北、四方八面大藏区的人们,一生中总有一次,不惜任何代价穿越雪山草原来到拉萨。对他们来说,时空的概念已毫无意义。在那些遥远而艰险的山路上,还有多少人正在这样日复一日地丈量着大地和岁月。只有到了拉萨,到了大昭寺、小昭寺,每一个人铺出的无人知晓的故事才有了终结。在那一代又一代人擦亮的石板上,这一播种虔诚、矢志不渝的仪式才变得庄重而辉煌。饱经折磨的身驱和所有故事到了这里,才随风而逝。佛的光芒此刻已完全穿透了贫穷,穿透了人体,把他们送到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言喻的世界。
当然,奔向理想世界的还有另一种方式,即逆叛。
我住在八朗学宾馆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来自藏北安多的姑娘,叫做达娃。那是一个像熟透的苹果,不,更准确地说像一只新出炉的面包那样,带着红扑扑的脸色,带着奶香的胖姑娘。一次我来前厅打电话时,我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大哥,你从哪里来?”
“长沙,湖南。”
她坐在一把画满图腾的长椅上,双脚晃动着:“长沙在哪儿呢?”
“在一个大活佛诞生的地方。”我逗她。
“大活佛?谁呀?”
“毛主席啊!知道不?”
“哦,知道,知道,你带我去好不好?”她突然站起来,走到我身边。
“带你去?”
“是啊!你带上我,带我走,做什么事儿也行啊?”
我吃了一惊,“什么”之后有没有这个“事儿”没听清。
“内地找工作也难啊!”我引开话题。
“你不是老板嘛,我就跟着你。再说,内地还有很多歌厅、舞厅,都需要姑娘去做小姐……。”我无言以对了,达娃的鼻息已暖暖地触及到我的脸上,我只能转身走回房间。
“我会唱歌,还会跳舞……”达娃跟着我走过来,穿过小院,走进走廊,她边为我打开房门,一边说:“带我走吧,好吗?”我抬头望着那双无邪透亮的大眼睛,说:“拉萨,不是也很好!”
达娃转身走了。
我在房间里开始清理像机,但人却很难静下来,远远地传来达娃似带忧伤的歌声,时续时断不知唱着什么,悠长回荡着不绝于耳,缭绕在我沉重的思绪中。
后来的几天里,倒是我总怕遇见达娃,我害怕那种热情和期待,我想,达娃应当不是叩着长头,而是乘汽车来到了天堂拉萨。但她为什么仍不满足呢?难道说,就是那首歌里唱到的“难道说还有……”,物质的诱惑力本来就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吗?没有人能够指责人们选择何种方式走向未来。在拉萨、在雪域高原很多时候,我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条游弋于远古海洋的小鱼,──那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而水却对鱼说“我看见了,因为你在我心里。”
叛逆的达娃,我只能默默地为你祝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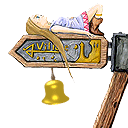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