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表示对歌曲的作者樊蔚源的感谢,在落霞妹妹的鼓励下,现将自己06年的文章《婆婆》贴上来,以示对乡亲的感怀之情。

婆 婆
1968年底,妈妈从省城下放到浏阳七宝山乡,我随即从大围山转点到七宝山陪伴母亲,我们母女就住在婆婆家。
妈妈下放的队是一个刘氏家族的大屋,一个队的人全都是姓刘。婆婆是刘家的长媳,住靠东头的两间房。我和母亲被安排住在婆婆家后院。穿过婆婆家的厨房门,经过一个天井,北头有两间小柴房,是我们母女和另外一位下放干部住的地方,靠南头有一个柴火灶台,听婆婆说,这房子原是给农忙时外来帮工的人住的,好久没有人住,只好用来放柴火了。由此可以想象,婆婆家原本也是有着不少田地的农户。
后来才听人说,婆婆家原本真是有几十亩地的,三十岁左右时她丈夫得病死了,她没有再嫁,独自一人苦苦地撑着那几十亩田地,还真是不容易。 婆婆自己没有生养过,带着一个孙子是从刘姓兄弟家过继来的,叫刘谷初,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谷初年龄比我还小两三岁,一岁时就过继到婆婆这边来了,是一个长得很俊的男孩,只是走路一瘸一瘸的,婆婆告诉我们,那是因为谷初三岁时被蛇咬了,请土郎中治疗以后总算保住了性命,可落下了这个终身残疾。 谷初生性活泼开朗,吹得一手好听的笛子,每逢下雨天或收工后,他的笛声能带给人们一种极美妙的享受,在那偏僻的山村里,可真算得上是天籁之音哪! 谷初脚虽有残疾,但非常要强,出工干活从来不落后于队上的强劳力,田里的犁耙活样样精通,爬岭上山比我们快得多,生产队也从来没把他当残疾人,都是按强劳力给他记满工分的。 婆婆有六十多岁了,身材矮而瘦小,背还有点佝偻,说着代客家口音的浏阳话,身上常年穿着一件士林蓝布衣衫,头上搭着一条家织布的手帕,布满苍桑的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一双非常有神的眼睛,好像人世间任何困难都不会留在里面。很难想象这个小个子女人的一生是怎样迈过那么多坎坎坷坷的。
穿过天井的另一张门,是婆婆家的猪栏屋。婆婆养了四头猪,都有将近百把来斤了,头头长得滚瓜溜圆。她每天忙进忙出主要是为着她的那几头宝贝猪。 有时我帮她抬潲桶去看她喂的猪,她会显得分外高兴,眼睛中闪烁着光亮,话也多起来,她告诉我有三头猪是给队上养的,然后指着一头漂亮的黑白花猪凑到我耳边悄声告诉我,这一头是她自己的,“莫同别个港(讲)呐,小亦哎(她是浏阳客家人,总是把“余”说成“亦”),队长同意我私家养一头猪,是把谷初子以后讨婆娘用的呢。”我点点头,那个时候农村是不允许私人养牲畜的。看着婆婆苦苦拉扯大的孙子已快到娶媳妇的年龄,队长作为刘氏家族的侄儿,暗中帮守寡多年婶婶这样一个忙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给孙子娶上婆娘,这就是婆婆的最大心愿。
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婆婆是一刻也不歇息的。每天天不亮,婆婆就在煮猪潲了。她说隔夜的潲猪不爱吃,必须当天煮,四头将近百把斤的猪每天要煮一大锅呢。等我们出工的时候,婆婆就背着一个大背篓,头上搭着一条白色长手帕出去寻猪草,这个时候,我常听到婆婆嘴里哼哼的不知什么调,可能寻猪草是她最轻松的活儿吧。晴天雨天,出工收工,常常会看见婆婆在路边、在田间、在山坎旁寻猪草的身影。婆婆还种了好多菜,除了自己吃的,剩下的也就是用来喂猪了。傍晚我们收工时,又常常会看见一大担柴火从山路那边移过来,只要看见柴担中间有一个小白点,我知道,那是婆婆头上的家织手帕。每隔三两天婆婆就要出去打柴,每天煮一锅潲可要柴烧呢。
我跟着婆婆去打过几次柴,她总在我的前面猫着腰走得飞快,手中的柴刀麻利地砍开前面的荆棘,一边滔滔的跟我说着请人介绍给孙子谷初相亲的事情,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她的身后,嘴里只能“哦、哦”的应付着,说不出话来,心里却暗想:“谷初还小呢,着什么急!” 上山后,婆婆总安排我在一块柴较多又比较平整的地方砍着,自己却钻到更陡峭的山坡上去了,看不到她的人却能听到她砍柴的声音。和婆婆一起打柴我可不敢怠慢,手握柴刀一刻不停奋力地砍着,太阳晒在背上火辣辣的,衣服湿透了,汗水顺着鼻尖往下滴,我也不敢歇一下,生怕落在婆婆的后面,也学着婆婆的用一条长毛巾搭在头上,既挡太阳又擦汗。婆婆就在不远的地方,隔不多久会听到她送一个“哦——嗬”过来,山里人都是这样打招呼的,我也会回一个过去,我们一老一小的声音在大山里回荡,传递着婆婆对我的呵护,传递着我对婆婆的感激之情。
想起第一次和婆婆一起砍柴我真是可笑极了,那次,我看看自己砍的柴估摸着有一担了,于是就找来藤条开始捆扎,在大围山那边我就跟老乡学会用藤条捆柴,把藤条的一端先做好一个环,顺着地面插进码好的柴火,然后拿起藤条的另外一头,穿进环中,用脚蹬着柴拉紧,顺势拧过来,将头子别到柴火里就成了。捆好了自己的柴,再听听婆婆那边,好像还没动静,我喊了一声:“婆婆,回啰!” 就听到婆婆喊道:“哦——嗬嗬,走哟!”于是两人挑着自己砍的柴,沿着山路走下来,看到婆婆走在我后面,,我心里很得意,有点沾沾自喜。 但不一会,婆婆就赶到我的前边去了,我看到婆婆的柴担捆得紧紧地,很整齐,走起来一闪一闪,神气得很,而我的三不六齐,随时有散架的危险。等我到达山下时,婆婆已没了人影,我放下柴担歇了一会儿,心想,不着急,反正和婆婆一样,我也砍了一担柴。当我歇了一气,又挑起那七歪八倒的担子上路走不多远时,却看见婆婆又朝山这边走来,我问:“婆婆,你丢东西了?”婆婆指指山那边说:“我还有一担柴哦。” 我愣了,啊!原来我努力砍好一担柴的功夫,婆婆竟然砍好了两担! 婆婆走到我跟前,看到我肩上那担歪歪斜斜的柴担,示意我放下担子,手脚麻利地帮我把柴担重新整理一下,将扦担拔出来再扦插一下,等我再挑起来时感觉舒服多了。回头望望婆婆,她正在快步麻利的又向山里走去,我真是打心眼里服了。从那次以后,我和婆婆一起打柴再也不敢有半点懈怠了。
每当傍晚收工后,在金色的夕阳映衬下,刘家大屋的屋顶上飘起袅袅炊烟,谷初的笛子会随着炊烟飘起美妙的乐声。 婆婆家的厨房和我们家厨房是挨着的,一到吃饭的时候,谷初和我常常端着碗两边走着吃,谷初爱吃我妈炒的菜,我却爱吃婆婆的蒸菜,那可是最初尝到的地道的浏阳蒸菜哦,不管蒸的是南瓜、扁豆、还是一小碗腌菜,总能让我胃口大开,有时婆婆也蒸上几条小小鱼,必定端过来和我们共享(山区吃鱼是很稀罕的),那木头蒸桶蒸出来的红薯丝饭的香味到现在还让我回味无穷。晚饭后,大家辛苦了一天,都洗完澡休息了,婆婆的厨房那边还传出有节奏的嚓嚓嚓的声音,那是婆婆用铡刀在切猪菜,谷初悠扬的笛声伴着这嚓嚓嚓切菜声,回想起来,那真是最美妙、最和谐,最动听的交响乐啊。
婆婆养着十来只鸡,平时总是攒着鸡蛋到供销社换点盐和日用品,鸡是轻易不舍得杀来吃的。可是那一次我却接连看到婆婆在不长的时间内杀了几只鸡。记得那天我收早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在天井里围着抓一只老母鸡,一见我,忙说:“小亦哎,快些帮我抓到罗!”我赶紧快步上前,帮婆婆把鸡围到旮旯里抓住送到婆婆手里,婆婆接过鸡,摸着它的羽毛说:“哎,莫怪莫怪,你本是人间一碗菜……”,我问道:“婆婆,今天么子喜事啊?生蛋的鸡婆也舍得杀?”“有卡(客)来哟”,婆婆笑盈盈地说,随即凑到我耳边神秘的说:“是来帮谷初子介绍婆娘的呢。”我点点头“哦”了一声。 婆婆急切地要给谷初娶媳妇是盼望早日抱上重孙子,是她不希望谷初重蹈她自己的命运;她担心别人会嫌弃谷初那残疾的脚,她害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 她想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帮孙子娶到婆娘这个心愿,才算是对得起死去的老公。 我明白了婆婆这个心愿,心中也开始为谷初的婚事操起心来了。 做媒的人来了几次我不太清楚,反正婆婆的老母鸡是眼看着少了好几只,谷初的婆娘还是没有着落。女方人家真的是嫌弃谷初那只一瘸一瘸的被蛇咬过的脚呢……
六九年的秋天,我随七宝山知青文艺宣传队踏上了三线建设的工地,我们队上好多年轻人都报了名,我知道谷初当时也很想去的,但终因自己的瘸腿没有报名。 修铁路两年的经历,让我在各方面受到很大的磨砺,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见《真情永存》一文),我竟然没有再回到七宝山当农民。
1972年11月我被招工到湘东铁路临管所,那时母亲已恢复工作不在七宝山了。 我到公社转迁关系时,又回婆婆家住了一宿,那晚我是跟婆婆睡的。 婆婆知道我这一走就难回来了,做了很多菜给我践行,少不了有我爱吃的蒸小鱼、蒸咸菜、蒸南瓜、蒸木桶饭(那次没有放红薯丝)……。 晚饭后,婆婆仍旧是在“嚓嚓嚓”的铡着猪菜,但却没有听到谷初的笛声,我在煤油灯下陪婆婆坐着,听她说着…… 原来我们修铁路走后,队上一下子少了好些年轻人,谷初觉得很没意思,加上后来好几次相亲都没有结果,生性活泼开朗的谷初也慢慢的变了,变得沉默少言;变得爱抽烟喝酒;变的焦躁起来,有时还对婆婆发脾气。 婆婆说:“你看啰,又到冬初子过边恰酒去了,港(讲)又港不得他,哎,冒的办法呢,小亦哎。”说话时,一脸的无奈。 我看到婆婆比以前苍老多了,眼睛也没有从前那么光亮,人比以前更瘦了,那双瘦骨嶙嶙的手只是在机械地抓着猪菜,切着、切着……,我无语,说什么呢? 晚上,和婆婆睡一床,听到她不停的咳嗽;又听到谷初很晚回来,很重的撞开隔壁的房门,如雷的鼾声……那一宿,我无眠。
睁开眼,天已亮了,不见了婆婆。我想起自己还要走十五里地去永和赶班车,赶紧爬了起来。 灶上的木蒸里,婆婆已做好了早饭,热着呢。婆婆去了哪里呢?依照以往的经验,我跑到后山的菜地里去找,果然,老远看见婆婆的蓝色士林布衣衫了,正蹲在地上呢,我心中一阵欣喜,跑过去叫了一声“婆婆!” 但我突然停下了,我看见婆婆不是蹲着,而是跪着!是的,她是用双膝跪在满是露水的地里,在寻猪菜! 婆婆听到声音,费力的想站起来,我连忙过去搀她起来,她抬头看着我,摇摇头说:“脚冒得劲哒呢,小亦哎。”我看到婆婆的双眼已经昏花,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光泽, “婆婆,”我叫了一声,摸摸婆婆那两条湿辘辘的泥裤腿,泪水已止不住流了下来……
我含泪告别了婆婆,离开了七宝山,离开了农村。 虽然是招工了,但我心中却很难高兴起来,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
回城以后的好多年,我仍是在迷茫中碰撞着,挣扎着,很累,很忙,…… 其实我知道这是给自己的借口,我一直没有回七宝山看望婆婆,心中却一直惦记着她,这位一辈子辛勤劳作,总也没有给自己理由歇一歇的老人。
直到1984年暑假,我们的孩子已经六岁了。我和广哥下定决心,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带着儿子来到了七宝山乡,我们来到了刘家大屋。
婆婆已经去世八年了。她真的是在有生之年帮谷初把婆娘娶进了家门,在谷初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的几天,婆婆安祥的离开了人世,她是带着微笑走的,她完成了她的最大的心愿,她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了。谷初的媳妇是一位勤劳、娴淑的女人,脸上也总是荡着朴实的笑容,大儿子已有八岁了,小的也有六岁,看着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我深深的吐了一口气,我好像看到了婆婆欣慰的笑脸。我为大山里的善良的人们祝福!
瑾以此文缅怀这位在大山里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婆婆。
2006.6.
带着六岁的儿子回七宝山

谷初一家人

刘家大屋的老乡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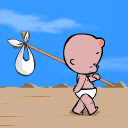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