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楼

——2009年09月17日01:33 雷 达
回眸60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着文学,而我们的文学也在不断地选择着自己在时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自身对时代最敏感的问题,这种双向的选择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焕发活力……
十七年时期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我们的作家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呢?艺术还有没有它自身特殊的生存秘密呢?当然有。不少作家受新生活的促动,探索和寻找到艺术地表现新生活、也适合大众接受的方式,把自己的创作能力和个性仍然发射到极为可观的高度,有的至今放射着夺目的生命之光,不能不令人惊叹。我可以开列出一个包括《青春之歌》《红旗谱》《茶馆》《创业史》《林海雪原》《苦菜花》《三家巷》《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艾青的诗》……我认为它们虽然充满内在矛盾,有其硬伤、局限性,但大体上在时间的河流中挺立住了。这是怎样的悖论和奇观啊……
……1978年9月2日《文艺报》在和平宾馆九楼集会,为《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写伤痕的短篇小说呐喊助威,这一举动震动了全国文学界……12月5号,在新侨宾馆……为一大批“毒草”平反的会,涉及作品极多,从《保卫延安》《刘志丹》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的《祝词》具有纲领性质,从此,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变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新时期以来的这30年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经历了三种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文化语境:第一个阶段在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与政治的拨乱反正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在相当长时间保持同步共进的关系;文学以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萌动,找到了代言人的感觉,文学反对瞒和骗,呼唤真实、大胆、深入地看取生活并写出它的血和肉的“说真话”精神。80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被大量译介进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碰撞激荡,使现实主义的独尊地位有所动摇,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局面。//第二个阶段在90年代,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而来,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趋向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和诗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在2000年前后至今,一切正在展开中:全球化、高科技化、市场化、城市化、网络化成为它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网络,被称为“第四媒体”,其无所不在的能量,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时空观和人的存在状态以及思维模式,也大大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
……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箝制,我们的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这30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
那么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有一种精神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自由和独立的存在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守持。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走向边缘化之后依然顽强地活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就不断地向世界文化和文学靠近和学习……就文本来看,也许突出表现在先锋文学中。比如,马原是先锋小说的开创者之一……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先锋作家那里得到了比较完足的实践。有人说,没有开放,没有向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学习,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学,不是没有道理;还有些外国文学翻译家骄傲地说,正是他们在实际上引领着文学的新潮,翻译家的语言甚至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风。
所以不夸张地说,近100年来西方文学的思潮在新时期30年文学中被中国作家一一模仿或借鉴过了。在小说界,普鲁斯特等成为中国作家学习的榜样;在诗歌界,叶芝等一大批世界诗人成了中国诗人的标杆和偶像;在批评界,原型批评学说,复调理论和狂欢化诗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都成为批评家学习和依凭的学说甚至理论资源。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这近30年一样,组成了一个光辉闪耀的星群……
但我一直在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索呢?或者说,有没有它的主潮?有人认为无主潮、无主题,我却认为主潮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那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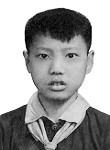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