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回城算是一种意外,也是一个必然。
1975年,和我同一批下乡的50余名知青中的最后一名战友也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离开了生产队。这时的我算是放下了一个心思。
当初来的时候,我们这批知青中有很多人都是身体不好什么的,没被第一批下乡的组织者批准的。是我借用自己学校革委会委员的身份,从学校的军管负责人、校革委会副主任手里磨出了一张参加内蒙古知青安置工作会议的介绍信,又取巧到当时的市学生管理机构“呼三司中学红代会”那里换得了一张更加“权威”的介绍信,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当年(1968年年初)的“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弄到一批下乡指标,二是为了见见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已经下乡了的那些先驱者战友们。
会上,我见到了77年秋天从北京第一批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的以曲折为代表的十名知识青年的代表王静植(女),当年11月份也是从北京到也是牧区的东乌珠穆沁旗插队的知识青年代表(名字忘了,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还有我们呼和浩特市首批到牧区插队的代表托娅(女,蒙古族)。
听他们讲到了草原的艰苦,更讲到了牧民的纯朴、憨厚与热情。我的下乡决心更大了。死活缠着内蒙古安置办公室的领导同意我们也到远离呼和浩特市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去插队。当时批了100个名额,后来到下乡时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各地要知青的热情也高,增加到了150名。分为西乌旗40名,东乌旗60名,东苏旗50名。我就在前往西乌旗的40名中(下乡时的实际人数达到了49名,再加上不久后其中一位同学的妹妹带了个伴儿自己跑来加入,总人数达到51名)。
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到了知青开始陆续考虑回城的时候,我作为发起者总不能自己先跑掉吧。于是一个个地送,直到75年全送完了(这里包括选调到了旗里或公社工作的情况。反正都算是安排了)。
送走队里最后一个战友,我开始考虑自己的路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宜什么体力劳动。早晚都得离开生产队去城里过的。但总还没想好该怎么回去。
这时候,后来下乡到队里的知青们来找我“评理”了,让我说说他们当中该谁先被推荐回城。
这下子我才意识到:这些后来的知青们干脆觉得我就应该是开始安排他们离队了!我自己似乎已经超出了被考虑的范围了!
加上这一年我连续几次外出参加了一些知青方面的会议,总是忙于受委托写一些稿件什么的,也没有机会去寻找回城的具体途径。
当然,在这期间的自治区知青代表大会上,几位知青发起建议成立知识青年自己的大学的建议我也参与了,对它抱的希望很大。觉得那才是自己的最好选择。但当时锡盟知青办不同意内蒙知青办用借调的方式让我先去参加筹备工作,怕最后我还会再回到生产队去。于是我就又回到队里去了。后半年没了什么音讯,这个念头就又淡漠下来了。
1976年初,公社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准备安排我到公社去搞“畜牧科研”。让我安心等待。我想这也应该算是安排了,于是再不作其他打算了。
接着,公社派我到宝昌去学习什么“土壤化验”,一周的学习班,我去晚了,只参加了最后两天的培训,领了一个搞化验用的小箱子就回程了。
路过锡林浩特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到盟知青办去看看。结果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去掉提议中的“内蒙古知识青年大学”(当时不知道全名是叫“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就要成立了,已经决定让我去担任学员兼工作人员。叫我立刻前往呼和浩特的加工厂知青办报到。
就这样,我匆匆忙忙地回到公社,向公社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由于当时只讲到“学制一年,社来社去”,所以没人和我争这个名额。很顺利地就得到了批准。再急忙跑回队里,没见到队领导,只遇到一个队领导班子的成员,把情况向他讲了一下,反正一年就回来嘛,也没作其他打算,收拾了两个小旅行包,一包是换洗的衣物,一包是那八本马列选集和四卷毛选。向还在队里的几个小知青打了个招呼,当天就到公路边上拦了一辆去锡林浩特的班车走了。再从那里一路不停地赶到了呼和浩特。
到内蒙知青办报到后,还有时间回了一趟家,弄了一套行李。然后就跟着车到了学校选定的地方----乌兰察布盟的凉城县岱海青年农场。
那一年的经历,我已经在拙著《开拓,在这版沃土》中给予了记载。
那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又招收了一届一年制的长训班,还是四个专业。我担任了政治理论专业的班主任兼课任老师。这个班没办够一年,由于大批知青返城大势的形成而自动破产,提前解散了。
接着,学校又办了几期“《毛主席五卷》学习班”,学期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我又在其中担任了一门课程。
就在这段时间内,学校决定为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由于我在授课,学校派了专人到我下乡的地方,把户口什么的办回来了,还拉回了剩余的、被不知何人瓜分后余留下来的可怜的家底。
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城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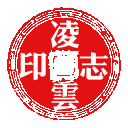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