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去了的福外上墙湾
人生,就象在大江大河中远航。虽然,航船最终要驶到终点,但远航中总有几个大码头要停靠,福外上墙湾就是我最早停靠,并且流连忘返的地方。
长沙是湘江边上最大的城市,福外上墙湾,就是长沙市河东区有名的西长街里的一条支巷。这里曾经是长沙最热闹的地方,它北接中山路,南与西长街相通,外延至五一大道,正西面对着一堵高墙,俗语称半边街。小巷只有四五米宽,以前是长条石铺路,虽坚硬但坎坷不平。很多地方由于时间久远,中间会有一条独轮车压出来的车辙。这个只有半边街铺的街道,一家挨一家,靠得很紧,每家都只四五米宽的门面,上下两层,又住人又要做生意,叫做前店后房。门店、房屋高低错落,大小不一。但那时候的人们,只有撞挤的热闹和居民的相扶相持,没有拥挤的烦恼。
这里离湘江很近,只隔一条小巷,从高墙两边的里弄里穿过,就到了河边码头。那时候沿江停靠着江轮,多数是运货的,也有运粮的。粮仓就在江河堤上,高大的皮带走廊,横跨在街道之上,从江里的船上向上面仓库提运稻谷。江边还有运煤的、运砖的、运木材的、热闹非凡。运大小商品的货船在江岸上一字排开,各式转运站在江堤上零零总总门庭若市。货船多以一两块长跳板与河堤相连,转运站的货物,靠人工肩挑背扛,把大小包裹从深深的河床下搬上运下,乱烘烘的,湿漉漉的,飞汗如雨,那场面热闹而悲壮。
福外上墙湾的周边,住着很多这样的小商贩和卖苦力的人们。我的舅外公一家,也住在这里。其实舅外公,是我舅舅的岳父,但他老人家把我和我的妹妹们,看得跟自己的亲外孙一样亲。
我记得小时候,长沙市区晚上没有电,舅外公经常会打着手电筒,不顾黑灯瞎火,带我们去小巷口的“横吞”担子上,吃摆在那里的“横吞”。有时候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热腾腾的小笼包子,就已经摆在了桌子上了。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舅外公亲手做的茶盐鸡蛋和五香鸡蛋,黄黄的、香香的、热执的、软软的拿在手里,还真的有点舍不得吃。
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福外上墙湾在我的印象中慢慢清晰,半边街,木板楼,石板路。拖板车的拖一路,叫一路:“买-----黄泥--吧!”挨家挨户停停走走;挑货郎担的摇着拨浪鼓,一声紧一声慢沿街叫卖:“拨咙---拨咙------拨咙咙!”还代收长头发;卖牛皮糖的铜器打击声,声声脆:“铿---铿—戚,铿---铿—戚!”;与算命先生的小铜锣:“叮---叮------当,叮---叮------当”此起彼伏,渐近渐远。如怨如诉,悠远深长…….
儿时的记忆:早春的甜酒、白粒圆;盛夏的白糖波萝纸包冰;秋凉的豆浆、油条;深冬的木炭烤红薯,是我们表兄弟、姐妹们最爱吃的名食,那形、那味、那熟悉的叫卖声,只要一想起,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叫着、喊着、吵着、要马上买着吃。有时候还有滋有味的跟着学几句:“波萝---纸----包--冰啦,才出来--的--热---包冰---啦!”,听起来好象很有味,很好玩。
其实,现在想起才慢慢体会到,这就是底层人民为了生活,无奈、且坚韧的声音。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文化就是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仁、义、礼、智、信”的信念中,生活积累而形成的。而文化名城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文明的坚持中成名的最好的见证。
现在舅外公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沿江河堤上粮仓早已被沿江景观带所代替,河对面的桔子洲也成了全国有名的桔洲公园。最近听说福外上墙湾,随着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拆迁改造,这是一件大好事,虽然,人们有睹物思人的情结,虽然,儿时与表弟,在河边游泳,在船上跳水的情景,还时有回想,但必竟事已境迁,历史潮流总会前进,就让我们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企盼过去的美好的每一天,都化成文化、文明的记忆,保存在祖国新建设的,钢筋水泥的宏伟大厦中,衍生出新的美好生活。
别了,半边街,福外上墙湾......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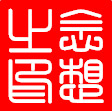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