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外来户(一)扫街的“大傻”
年末岁初,许多农民工将踏上返乡路途。但灯火居住的小区却有些进城谋生的农民春节不返乡,成为小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清洁工,保姆,发廊女,果贩等,姑且称之“外来户”吧——跻身“城里人”中的“外来户”,个中甘苦几人知?
冬天早上六点钟,天还没亮灯火就被楼下清洁工“大傻”的叫骂声闹醒了。“大傻”就象报晓的公鸡,乱骂一阵在路上乱扔垃圾袋的人后,开始了例行清扫工作。
铁路住宅区还残留一些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水电、道路等设施仍由铁路水电段、房建段负责维修管理,各小区由房建段聘请清洁工负责日常清扫。每户每年从工资扣48元卫生费。
被人称为“大傻”的清洁工就这样在三年前走进人们视线。据说“大傻”是小区某女士轻度智障的哥哥,年过四旬在农村还未娶上媳妇,年迈的父母过世后“大傻”无法过活;某女士只好托人弄进来当清洁工,好歹每月有四百多元工钱挣碗饭吃,还有房建段修的垃圾站小屋栖身。
“大傻”虽然智商较常人低一点,做事下死力气真没得说。作为廉价劳力,他一人要负责2平方公里地面日常清扫,每周还要清扫一次各楼楼道(不过他现在也学“滑”了,数周不上楼,居民只得“自扫门前雪”了)。每天天没亮,出门晨练的人们就发现“大傻”拖着垃圾车扫地,干到中午才回到垃圾站煮点烂菜叶泡饭吃。饭后穿着不知哪捡来的破铁路制服大衣,蜷在墙根晒个把时辰太阳后,“大傻”又抡开大扫帚在小区再清一次垃圾。有时白天下雨不能扫地,晚饭后散步还见“大傻”路边积水中扫地,还真有点任劳任怨的劳动态度。只可惜“大傻”这样的临时清洁工每天工作十多小时,却没处评“劳模”。
“大傻”好象既不觉苦,也不觉累。比起家徒四壁难以谋生的乡下,能从事清扫这简单劳动,烂菜叶煮泡饭有饱饭吃,有垃圾站栖身,也许是“大傻”一生中最惬意的生活。
附带说一句,房建段卫生监管员来抽查卫生时称,只要求他每天清扫一次,没人要求他没日没夜干。也许孤独的“大傻”生活中没有其他乐趣与嗜好,用劳动来打发时间?自觉自愿如马克思云,“把劳动当做人生的第一需要”?当然,雇主都会喜欢这种白痴似的廉价劳力。
过去人们说城市是个“大染缸”,连“大傻”也多少沾染些“刁民”的习性。有时真怀疑他就是那个风里雨里扫街轻度智障的人。
好几次见一米七多个头、黑瘦的“大傻”戴着捡来的旧铁路大盖帽,穿着满是油垢的旧铁路制服大衣,胸前佩着“清扫员上岗证”向小区门口菜贩收钱——谁在地上乱丢烂菜叶罚2元。没有收据,不知谁赋予他这种权力?也许“大盖帽”满街飞能唬人,还真有卖菜的农妇乖乖向他交过钱。也有碰钉子的时候。有个强壮的郊区菜农不服罚款与“大傻”扭在一起,“大傻”被摔来摔去只有招架之力,明显处于下风,只不过菜农不谙摔技没把他放倒而巳。这时有好事者(估计是乱扔垃圾袋被“大傻”叫骂者)告菜农,“把一条腿一伸再一推就赢了”,菜农受点拨一伸腿把“大傻”摔个狗啃屎,扬长而去。
好久没见“大傻”戴着“清扫员上岗证”罚菜贩款了。他的垃圾车上搁个装废品的大纸箱,估计每天扫地捡来堆在垃圾站旁的废品是笔不菲的收入吧?兴许熬上几年回乡娶房二婚头媳妇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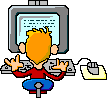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