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下放到洞庭湖边的一个丘陵小村,小村正对着洞庭湖的一个河套,远远就能看见一大片美丽幽蓝的湖水静置其间,村里有二十几户人家。
像翡翠一般的山丘“U”字形的将一湾宁静、梦境一般的蓝色湖水镶嵌。山丘上长着一些不成材的灌木杂树,封山两年灌木杂树就将山丘裹了个严严实实,这些灌木杂树正好是队里人家的柴草。山是根据实际情况轮流封育的,人民公社时,没人敢随便上山砍柴,要等秋天队里按照各家的人口、劳力等情况将那些山头划分给大家。
秋收后,去洞庭湖修大堤称为修大水利,在本区修塘坝称为修小水利。柴山分好,修大水利前各家可请几日假,不出集体工,去山上砍柴。柴砍了回来,与田里分的稻草一起,算作是一年的燃料。那时决不会因在稻田里焚烧稻草,影响飞机起航。贫下中农居家带口,还要养猪、蒸酒,特别珍惜这些灌木茅柴,早早地乘秋天树还没开始落叶,把它们连茎带叶全砍了,只摊晒一两天就挑了回来,当然那样挑柴火会重很多。他们砍柴很里手,将那些山头收拾得干干净净,像剃了和尚头一样光秃秃的。
知识青年们还不懂得过日子,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那么急迫的去砍柴。秋一日一日地往深里走,眼看过了寒露又过霜降,分给我的那一块原本青绿纲蓝密密的灌木丛,枯黄的树叶厚厚地掉了一地,只留下枝杆稀稀疏疏零落在山丘。即便是被砍过的那一小块,因技术实在不高明,也像癞子脑壳。
十月里我邀了隔壁队的一个知青,跟队里请了两天事假,决定将那些柴草解决了。去借砍柴刀时,哑巴叔很热情,他帮我们将俩把柴刀磨得黑锃锃闪亮闪亮,还为我们准备好挑柴的扦担1。比划着要我们砍柴时小心,别砍着手脚;砍柴时,砍干净些;实在挑不动,告诉他,收工时帮我们顺便一担一担带回来。
我俩肩扛扦担,手拿柴刀一路说笑着上山了,不像是去砍柴,那心情倒像是去“秋游”。
上到那山,我俩没有认真砍柴,而是躺在面向洞庭湖的山岗上,舒展着身体,晒着暖暖的太阳。深秋,天气真好,阳光展开灿烂的微笑,太阳雨一阵一阵地落到地面。天空泛着瓦蓝,像水刚洗过一样,极目久望,心也变得宽广无际。成群结队的大雁向南飞去,杂林中黄鹂、斑鸠、布谷、麻雀……鸟儿们在举行音乐会,高低抑扬、清清朗朗,鹦鹉在表演自己的歌,在山野它不必学舌。我们享受着看似平淡无奇生活,静观天地与人世,慢慢地品味生活的美丽与和谐,和最深最平和的快乐。我俩谈了些什么?整整说了两天。
两天,聊天为主,既然是请假砍柴,总还是要砍一点做做样子。砍柴、捆柴、挑柴平日见贫下中农干得那么轻巧的活计,我们弄起来并没有看起来那样简单,要娴熟肯定得下点功夫。我俩折腾了两天砍得像癞子脑壳不说,还只砍去了分给我的柴山的一小片,砍下的柴火零零散散铺在山头。第二天去归拢打捆时,捆柴费了我俩不少的脑子,首先我们无法将那散开的稻草绞成绳子状;好不容易将稻草绳绞好,捆柴可不是好玩的了,抱起那些柴,不是荆棘刺了手便是硬柴弹了脚,将就着松松垮垮捆了几捆柴,被兰儿批评说要是让她爹捆总共才只是两捆。确实是的,我自己捆的柴,一捆一天就烧完了,后来到哑巴叔家拿的柴火一捆要烧好几天。要叉起那些柴火真是太难了,我学着贫下中农的样子,用扦担的一头猛的扦进一捆柴里,再使劲举起来,去扦另外一捆柴,但我们捆得太松垮,那柴在扦担上根本就挂不住,“索溜”一下就溜到了扦担中间,打到我的背,另一捆柴无法扦上,只好放下重来……反复多少次,怎样才挑起那担柴的,已经想不起来,只留下使尽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挑回来一担柴的记忆。那些天,我俩砍柴的经历成了全队人出工时开心的故事。
后来,哑巴叔的女儿来跟我说,哑巴叔愿意帮我把柴山收拾了,柴火砍回来,全放到他家里,我要烧时去他们家拿。还说我们这样迟迟地不把柴火砍回来,叶都落了,还砍不干净,可惜了那些柴山。如果我愿意,以后每年他都帮我砍柴,柴火放他家,够我烧就行。那时,每年冬天我们要上洞庭湖修堤修水利,至少两次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个人在家里吃饭的日子也并不是很多,又不喂猪,烧不了多少柴火,他得了我的剩余柴火,我省了砍柴的劳役。口头协议达成,以后的几年直至我回城都这样,但我心里总不踏实,总有一种地主老财剥削贫下中农的感觉。
还有一件事情也使我有剥削贫下中农的感觉,那就是打米。口粮是队里分红的谷子,从队里粜到的口粮,要到大队部去加工成大米。去大队部的加工厂打米要走十来里的山路,一百斤的担子我挑不动。这事有不少贫下中农愿意帮知识青年的忙,我们出打米加工费,他们帮着去打米,然后获得打出的碎米和糠来喂鸡喂猪。几乎每次都是我的米还没有吃完,就有人来打听,要帮我去打米,还鼓动我打米时多打一次,因为多打一次米就精细些,糠当然也多一点,加工费长两分,由我付。
蹉跎岁月中村里的那些小事,深远而悠长地过去几十年了,带有那么鲜明的时代烙印,带着浓浓的乡情,在我的记忆里仍相依相存地与我和谐相处,那么生动。我时常思考着:是我剥削了贫下中农,还是我们各取所需;下放农村是知识青年接受了再教育,还是我们互相关照,共同学习,提高思想觉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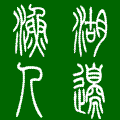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