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截 红 麻 绳
刘新华(武冈知青联谊会会长)
这截红麻绳是一个死去30多年的上山下乡女知青留给我的。
她叫张慧春,中等身材,长着一张让女同学嫉妒的脸。因与我小学、初中同窗,6 9年下乡又分在一个生产队,就被同学们双双封了个“九年半”的绰号。读书时我成绩比她好,又住在隔壁街,小学时,她主动和我组成一个课外学习小组,轮流在两人家里做作业,当然我是组长。她很调皮,经常不是藏我的铅笔就是偷我的橡皮,看我找得团团转,她却在一边偷偷笑。读初中了,她比我懂事早,不再在别人面前和我说笑,但在无别人的地方,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总是瞅得我脸红心跳。初中在复课闹革命中读了三年半,毕业后,她父母双亡本可以不下乡,但她硬是报名下去了。
下乡第三天,大队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她人漂亮,喉嗓又尖又亮,理所当然扮演了主角白毛女。曾和她登台对唱的我,因相貌平平,只演了一个民兵甲,端着木枪在台上从左至右走两次就完成任务了。排练了半个月,她没和我单独说过一句话。
正月初一,在大队小学操场的土坎上进行首场演出。山里人看戏难,又见是城里知青唱主角,人来了一操场满满的。临开演时,她突然慌慌张张找到我,说喜儿用的红头绳丢了,要我帮忙想办法。那时穿毛线衣的人很少,我只好扛着张画得红堂堂的脸满场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纳鞋底的大嫂,向她讨了一截细麻绳,又找到了一个老师用红墨水染了,弄得满手通红交给她。看到我这模样,她笑了,用那根红绳子在我手上轻轻打了一下,低头说:“谁叫你是‘九年半’”!
演出大获成功,“九年半”从此在乡里闻了名,全公社都晓得有这么一个长得漂亮唱得好听的城里知青,公社大队开会,都不忘叫她唱一段《北风吹》。
三个月后,又发生一件事,使她名气更震。插早稻时,她的左脚被瓷片划伤了。一日春工十日粮,为了不耽工,她把脚用布一包,放进一个小木盆里,边扯秧边移动木盆,坚持到插完秧。这种事当地农民都难以做到,在全公社的春耕生产总结会上,公社书记把她大大表扬了一番,真叫我们羡慕佩服了好一阵。碰巧,不久后一天,我在山里砍柴,突遇一场山火,为了救火,我烧焦了一撮头发和一截眉毛。于是,在5月份召开的全县知识青年积代会上,我们两个“九年半”都成了代表。我和她本住在隔壁街,可在那个最敏感的年代,我不敢和她会上一块坐,也不敢会后和她一起走,只是见面笑一下,又赶紧低头走开。
9月中旬,县城几家工厂来招工,她被推荐参加体检,而我呢,有一次看到另一个女同学把无盖的便桶放在床头,说了句“淤桶放在屋里太臭了”,碰巧被生产队贫协组长听到汇报上去说我嫌贫下中农屋里臭,是资产阶级思想,就这样我的名字被涮下来了。
那天下午,大队开了全体知识青年参加的欢送会。我心情沮丧,坐在一边一句话也没说,散会后,我和几个同学送她到队里,在她的一再挽留下,我们在她家吃夜饭,四个人,四斤米,还有队里分的4块豆腐邻居送的一大把豆角,这是知青中难得的一餐饱饭。我虽肚子饿,吃了一碗便不想再吃。她抢过我的碗,给我盛了满满的一碗,送饭的时候,她的手明显地停在我的手掌上,那湿润柔滑的感觉刹时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一抬头,碰上了她的眼光,虽只一瞥,我却分明看见她的脸腾地红了,眼里闪着异样的光,辣辣的、润润的。
直到夜深,我们才离开她的家,她送到院门前的水塘边。月色如水,把满垅的禾苗泻成了银色。蛙鸣如鼓,好象我们的心情起伏不平。其他同学已走远了,只剩下我和她仍在不声不响地走,越走越近,近得彼此的粗重呼吸都清晰可闻。可我一直没好意思回头看她,只是脚步越走越慢。已到公路上了,我颤抖着声音说:“我走了”。她嗯了一声,好一会,她把一样东西塞在我手里,说:“我到城里就给你写信”,那声音分明也带着颤音,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我低头一看,手心里攒的是那截红墨水染的麻绳,我急忙抬头,想喊她,想拉她,想仔细看看她,但我终于没有,目送着她披着月色,摆动着两根长辫子,渐渐融入了飘着稻香的田野。
走的那天,我怕人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感情,就没有去送她,铸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听说,她是坐大队手扶拖拉机,由生产队长送进城的。
过了3天,生产队长回来,带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噩耗:她死了。据队长说,本来在进城前她就说心里不好受好几天了,第二天体检时怕影响体检结果,她没敢跟医生说。体检完后她去看病,年轻的医生说是感冒,开了几片药。当天晚上她就突然晕厥过去,抬到医院,才发现是钩端螺旋体作恶,可为时已晚,第三天,她没来得及看见招工录取通知书就死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那次脚伤坚持出工感染下这种致命病的。
消息传开后,队上的贫下中农大婶、姑娘们都哭得眼睛红红的,队长也破天荒地喝得酪酊大醉,睡了一整天。
这天晚上,我坐在床沿上,生平第一次哭了。半夜了仍然睡不着的我翻出了下乡时舅舅送的笔记本,写下了这辈子的第一篇日记,然后将那截红麻绳夹进本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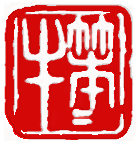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