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甸梦寻
作者:都梁乡士
九月,是登高怀人的季节。踏着肃杀的秋气,我走进大甸,走进一个沉甸甸的梦境。
对着车路,一栋红砖房子呈“丁”字形横在路边,与我一起来的杨式忠说:“走,看看现在这栋房子是谁在住着。” 他是当年那304名中的一名,在这里十几年呵,他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俩轻轻地走进去,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人,也没有声音,一长溜房子,都是关着的。四十年前,304名知青从城里下来的时候,就是吃在这里, 住在这里,劳作在这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满了他们的足迹,印满了他们的欢乐 ,也印满了他们刻骨铭心的痛苦。他说:“那时候好热闹呵,想不到现在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你们一来就有砖房子住?”我问他。
“哪里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来的时候住的是茅草屋,这些红砖房子是1973年搭帮福建的那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告御状以后,上面才给了点钱修起来的。那时候,你知道么--”
在他的感慨中,我俩正准备退出来时,顶头的一间房子的门打开了,两个小妹子,大的十来岁,小的也就七八岁吧,冒了出来,式忠说,在这里,所有知青的后代耐不住寂寞,全都外出打工去了。那么,她俩从哪来的,搞不清了,也没有必要搞清了。看着她俩惊奇的眼光,我们默默无语,退了出来。
一抹斜阳,懒洋洋地照了过来,为这栋房子增添了一点亮色,却依然掩盖不住它的破败,房子檐口上的青瓦已掉落在地,乌黑的玄皮露了出来,软软地垂着,随时会掉下来。岁月流逝,如今,我作为知青的同道,却在这里,不合时宜地“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值得感慨的还有,在几座用红砖砌成的房子里,没有门,更没有锁,摆着几台铁器制成的揉制茶叶的机械,尘灰蒙蒙,铁锈斑斑,漏雨的房顶,把地面滴得一片潮湿,外面青蒿掩径。青蒿中,还有一些烧剩的煤炭,堆在空坪上,任风吹,任雨淋。一切在无语地证实着知青当年在这里时的火红,也在诉说着今日的荒凉。这些铁器机械,要是有人拿去做废品卖,也还能卖到几个钱的。我想,在城里那水泥板块包围的地方,有卷闸门,有防盗门,
当式忠导着我一户一户走访的时候,一位老知青的老伴正挑着一担水,一步一步,缓缓地踩着泥泞,走了过来。水,浑浊得看不到底。就是这样的水,还是从四五里外挑来的。我没有记下她的名字,却记下了她的话语:“现在,我还只有五十多岁,还挑得动,要是再过一二十年,挑不动了,只怕连这样的水也吃不上了。”四十年,对人类的历史来说,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大半辈子光阴呵。如今,国家科技己经进步到让人从地球飞到了太空, 至于什么有线电视,无绳电话,就更不用说了,就仅仅说喝水吧。如今城里人一仰脖子,就能很随意地喝到纯净水,一拧水龙头,就能潇洒地用透明发亮的自来水冲洗厕所。可是,在这里,在这经过知青四十年奋斗的大甸,饮用的还是这样浑浊的田坑里的水。还要多少年的操劳,才能换来一担水的享受呢?
“我们种下的是龙种,我们收获的是跳蚤。”我想起了过来者写的回忆,知青们下到这里的第二天,就头顶蓝天,脚踩荒山,投入了改变荒山的战斗,用锄头,用铁镐,更是用在革命口号下激发出来的革命干劲,“重伤不下火线,累死不叫苦。”仅几个月时间,就把一座座荒山变成了一层层梯田,种上了棉花,烤烟和茶叶,同时种下的还有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创业初期,他们每天付出的是超负荷的劳动,而吃的饭菜,却是限量的,一天一斤米,每餐一个菜,不是南瓜,就是白菜,要不就是酸盐菜,还有的是没有一点油星的盐水汤。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连这样的生活也被搅得不安宁,有些知青流下的不光是滚热的汗水,而是殷红的鲜血!
穿过茶叶丛,我俩很随意地走进一栋红砖房,式忠告诉我,这里名叫鸟止界,意思是鸟飞到这里就要打住,再也飞不动的穷地方。当年一部分知青就是落脚在这里,这些房子就是当年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修起来的。
长长的走廊,是十几间单间,顺手推开一间,没有一个人,再推开一间,还是没有一个人,房间那简陋的摆设,吸引了我的目光,靠窗一张长条桌,上面满是灰尘,靠墙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层稻草,稻草上放着两只竽筛,靠门边的地上堆着一堆还没有脱粒的包谷。走廊上几件还滴着水的湿衣服挂在那里,证实着这里还住着人家。
式忠老兄放开喉咙大喊:“有人么--?”
几声呼喊,终于引来了回音:“是哪--个?”
声音是从屋外传来的。随着声音, 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走了进来,
“呵,是老--艾,艾治民。”式忠热情地为我介绍。
“我去把老婆喊回来,”不大一会,他的老婆也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的老婆是一个农民。朝夕相随,在这没有水,没有路,也更没有人作伴的山旮旯里,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整整四十年,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儿女,养大了儿女,可儿女却守不住寂寞,走了,到外地打工去了。留下的还是他们俩口子,除了他俩,还有一位知青李如海的孤坟。离离荒草,冷冷秋风,伴着他们,度过了四十个春,四十个秋。
我刚要问候,老艾先开口了:“听说你们在城里编了一本知青的书,可我还一直没看到,要是看一下······”我忙拿出《武冈知青回忆录》来,递给他。他把手在衣服上擦了两下,接过书,打开,看了起来。他老婆头一歪,紧靠着他,一起看了起来。他用手指着书上的照片,对老婆说:“你看,这是场里三十周年大庆的时候,老战友来了,在一起拍的照片。”看着照片,我想起我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台照相机,我掏出来,说:“难得来,拍张照片吧。”
室内光线太暗,我提议到室外照。在室外的茶树丛中,老艾说:“就到这里拍吧。那年三十周年场里大庆也在这里拍过。”说着目光深情地看着这片枯黄的茶园。
我端起相机,选择好角度,正要按动快门。老艾摆摆手,要我停一下,他走过去,拿起那本书,两只手抱着,放在胸前,式忠说:“这样子不好看,你要把书拿开才好。”
“不行,这是写我们知青的书,我就是要放在这里照。”他说着,把书抱得更紧了。
一本普普通通的书,他竟然看得这样重,可见“知青”在他心中的位置。我心里滚过一股热流,对着他,对着这本书,也对着当年的一段历史,庄重地按下了快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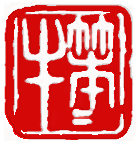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