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桃花水
30多年前,我在湘南边陲插队落户,我住的村子后面有一条明净的溪涧,溪水淙淙,携着十数条相交织的涓涓细流蜿蜒穿过河洲上翠色逼人的甘蔗林,绕过一座座绿树环合的村庄,一去十余里与流经桃川的桃川河相汇。
溪水不深,谷底铺着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村里人去冈垴上放牛、砍柴、割茅草;背着藥篓子的老郎中上山采药,只需挽挽裤管便可涉水而过。慵慵夕阳下,溪水羞涩地低吟浅唱,矜持得如同待字闺中的小女子。插队的时光,便伴随着这条恬静的小溪,日复一日地匆匆流逝······谁也没有想到,五月里一场暴雨,使得平日温顺有加的小溪忽然变得暴躁起来,浑浊的溪水像是桀骜不驯的悍妇,携裹着大山上的枯枝败叶嘶鸣狂号,奔泻而下,两岸成片的甘蔗林横遭淹没;通往猫崽山的小木桥被无情推走;洲子上牧鸭老人栖身的小窝棚也被冲得无影无踪。村里人要上山砍柴、放牧、给冈垴上成片的包谷地间苗、施肥,却为这肆虐的洪水所阻,人们只得望河叹息。
幸得几天后,小溪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它不曾有过恣肆狂放的日子,依旧如娴静的村姑般,轻轻吟哦着一首亘古不变的古老情歌,叮叮当当地在河洲田畈间流淌。
村里人说,一年一度桃花水,都几辈子了,小溪就这脾气。
闹“斗批改”那年春上,我忽然病倒了,脚沾地就痛,为了挣得那每天七分工换口粮谷子,我不得不忍住疼痛,每天和社员一起扯秧、插田、出牛栏,咬紧牙关不知拖了几日,终于支撑不住,连路都走不稳了。白天,同队的知青都出工去了,我一个人无奈地躺在床上,几只饿晕了的老鼠鬼头鬼脑地从门洞里窜进来,肆无忌惮地噬咬着屋角落的一堆红薯,我恨不得一砖头咂过去,可是毫无力气,正没处发作时,窗外忽然风生水响,一会儿便 听到河边甘蔗地里有人大喊大叫,情知是涨水了,心里便有些惶惶然,正惴惴不安时,出工的知青陆续回来了,大家见我躺在床上爬不起来,顾不上做饭,连忙把村里的老郎中请来了,老郎中看过伤势,又问了起病的时间,半天不吭声,只是端着烟锅子怔怔地望着窗外。同学们催他赶紧下 药,他吧哒几口烟,终于叹了口气说,还是趁早送桃川医院吧。原来,老郎中是靠敷草药治病的,可小溪上的木桥刚起水就被冲垮了,没法上山寻药,几个同学二话没说,很快借来竹竿扎成担架,忍住饥饿跋涉十几里山路,连夜将我送到桃川医院。
同学们白天出工,晚上轮流到医院照顾我。手术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忽然从梦中醒过来,是被窗外一阵高一阵低的哭声惊醒的,我问在一旁守候我的同学是什么人深更半夜哭泣?那位同学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说,都是让这桃花水害的······
原来,隔壁病房晚上住进一位产妇,她家与桃川仅一水之隔,因吃晚饭时突然发作,她丈夫与家人赶忙扎马轿抬起她直奔河边渡口,平日里清澈如镜的桃川河突然变得暴戾凶狠,船家望着湍急的水势不知所措,这样的场面,稍有不慎都将酿成惨祸,有经验的船家是不会贸然行事的,可面对眼前痛苦万状的产妇,看到一双双充满渴求的眼睛,老船工豁出去了,二话二话不说就招呼人上船,起伏的浪头一阵高过一阵,像横行无忌的脱缰野马,搅得小河惶惶不安,战抖的渡船仿如一叶浮萍,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好几回将到对岸,却又被排空浊浪推搡下去了,老船工凭着经验与勇气,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长篙前遮后挡,忽左忽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船撑到对岸,可这时产妇因受了惊吓,早已胎死腹中。
我挣扎着爬起来,趴在窗口看去,原来医院后门紧挨公路,公路那边的山坡下有一间没有门的土砖房,里面一灯如豆,闪闪忽忽,死婴就停放在那里,风阴阴地吹着,又送过来一阵阵凄凄的啜泣······
我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就出院了,因为紧张的双抢战斗已经开始,如不趁机多捞点工分,明年的口粮谷子势必发生危机。那时桃花水早退了,可它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却许久了也不曾抹去。。。。。。 (原刊《湖南邮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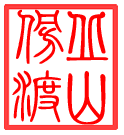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