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重阳节到来之际,发表此文兼作缅怀亲爱的母亲!
苦乐拾忆母待客
我是个经历了上个世纪那段为伟人倡导的“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吃不饱瓜菜代”苦日子的人,而今每当看到听到妻以及小区内的女人们面对菜市场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景气却老是抱怨不知每天该买什么好吃什么好,以及家来客人时不知该如何满足客人口味而犯愁,我便会想起先前的苦日子时代里母亲常为家里来客没好吃的招待而犯愁。
母亲是个好体面的人,再穷再苦即便让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在人前争份脸面。每个春节里亲戚们来家吃年饭,自然得讲讲体面烹几个菜。可那时候不用说今天菜市场应有尽有俯拾皆是的山珍海味不见踪影即使有也买不起,就是几个家养鸡蛋也是十分珍重,甚至连今天许多的小菜诸如黄芽大白菜也只能是年节里或办大喜事时的奢侈品。然而母亲心灵手巧,翻着花样一席桌上竟要烹出十个菜来,圆亲戚们一个十全十美的吉利。诸如一个白萝卜、一蔸大白菜梗,她横着切竖着切斜着切,切出大片子切出小片子切出大丁儿切出小丁儿切成粗丝切成细丝切成三角切成菱形,调成各色各状的菜,咸一碗淡一碗酸一碗甜一碗干一碗汤一碗炒一碗炖一碗,至于佐料,无非就是一点儿胡椒粉一点儿八角粉再称几两黄豆酱。就这样,席面上,姑爷表兄弟们端起家酿的红薯酒,喜洋洋的盛赞母亲:“三舅母真个好手艺,每年都能煮出这多好吃的菜呢!还是来三舅母家最好了!”获得盛赞之下的母亲,其实我最清楚她有多苦,因为每每来客时,是父亲出陪,而我下厨帮母亲打下手,都听得母亲小声又小声的嘀咕:“唉,能有什么煮啊!”“唉,家里什么都冒得,如何出得客呀!”
年节如此,平常更难,不用说吃不到一日三餐白米饭,就连杂粮红薯也保证不了不断炊,“吃不饱瓜菜代”往往也成奢望,而且尤其又是到得了七十年代那割资本着主义尾巴自留地里的菜蔬都要让干部们统统拔掉三餐只能熬清汤咽饭,鸡鸭要限养集市上鸡蛋鸭蛋要没收要作投机倒把处罚作资本主义批斗的时候,每到三四五月青黄不接的月份里,母亲最怕的是家里来客。客来了,一家人强装喜悦相迎,母亲在红薯鼎锅里蒸一碗米饭专门给客吃。桌面上,客人不好意思一个人独吞,这时候,我或是父亲往往能荣幸地从中分得小半碗米饭以充陪客的意思。而母亲,则从来就不享受这份荣幸,还要做出一副对米饭不屑一顾自己忒爱吃这杂粮粗食的样子来。至于席上的菜,母亲则是将攥了一次又一次的几片咸肉或是一个煎鸡蛋,切了炒了加在一大碗豆角苦瓜或萝卜白菜面上。席上,父亲母亲一个劲的劝客人夹这少得可怜的一点荤菜吃,自己则不吃。然而客人也知趣懂味,不会大吃,只会作作回报主人盛情的样子夹个两三片吃。客人走了,席撤下了,母亲立马便将客人吃剩的几片肉从菜碗里拣出,洗洗,重新腌上盐,再焙干或晒干,再收起,再作下次来客时待客用。
母亲的节俭,母亲的善于持家,母亲的从未怠慢过任何亲戚朋友,在我们的湾村里在我们的亲戚朋友中,是有口皆碑的,博得了一个贤惠的好名声。然而,这一好名声却一度毁在一次待客的尴尬中。
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割资本着主义尾巴大批资本主义的某个冬天,母亲的一个表弟领着两三个人因远行遇夜前来我们家投宿。母亲的这个表弟的父亲在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据说家境在他当地算是比较好的。事后我们听人传说,当时母亲的那表弟在路上就跟同伴们夸下了一个海口,说是他的表姐是如何如何的贤惠和待客热情,到表姐家必将得到如何如何样的好酒好饭好菜款待。那天我刚好在家,记得母亲的那表弟领着一行人叫着姐姐进得我们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一家早已吃过晚餐。突如其来的表亲,且还带着两三个生客,一时叫我们不知怎么办才好。饭还好说,还在下半年在冬季里,再怎么缺粮也不至于家里就没了这一餐三四个来客的米煮饭;小菜也好说,扁角旮旯地里多少还有点没被干部们拔光的萝卜白菜;只是荤菜,家里一点儿也没有!很少光临的表亲,何况还领着两三个生客,怎可怠慢得?那晚,急得母亲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一边叫父亲和我热情陪客,一边慌忙出门往湾村里去借去找能用的荤菜。可是找遍了一个村子,只找来了两根干腊猪骨头,骨头上几乎没什么肉。母亲生不出法子来,只好将就着把这两根干腊猪骨头敲碎斩碎,和着干辣椒做成一碗所谓的荤菜,再煮两个小菜和一个汤,倒上几杯红薯酒,让父亲相陪,就这样倾其所有款待他们。当晚一夜无事,母亲的表弟他们吃了饭后在我们家宿下直到次日早上辞别,也没表现出不高兴。但事后不久就从其他亲戚口里得知,母亲的这个表弟放出话来说,没想到我母亲竟用一两根干寡骨头剁碎招待他,让他在朋友面前倒尽了脸,说不起大话了,他发誓这一辈子再也不登我们家的门!母亲的这个表弟真的说到做到,打那以后,着实再也没来过我们家。
往事越过,一晃经年,苦日子终于过完了,改革开放让人们尽皆过上好日子,进入了因物质生活丰富而愁得不知吃什么好换什么口味好了的时代。这似乎应验了一个道理:人总在矛盾中过,社会总在矛盾中前行。过去,因穷因苦而愁,现在,却又因富得流油好得不知吃什么好而犯愁。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一年里难得回几次家,久未见到他们了便想他们,希望他们能得空回一回和我们团聚。可他们一旦回了家,我们又为不知办什么给他们吃让他们高兴才好而犯愁。所以每当妻为此犯两难的时候,我便对她说:“别老嘀咕了,他们没得空不回来就算了吧!”
不久之前,我曾在一所包吃包住生活办得不错的民办学校工作过。当有一次用餐听得几个年轻老师埋怨食堂天天几乎都是这些菜叫人吃腻吃厌了的嘀咕声,我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们说:“你们还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呢,这样好的菜肴还说不好吃。我在你们这般年纪时,不用说这大鱼大肉,竟连小菜饭都没得保障呢!”可他们却亦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敬我说:“嘻,主任您这话就不全对了,什么叫做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呀?那只能说,谁叫你们那一代生在了那个苦时代呢,而我们这一代却命好,偏偏生在了这个任我们挑食的好时代。我们这正是知福呢!”我那次本来很是想因势利导开导一下这些刚为人师的后生伢妹子,没想到反而被他们呛得无话可说了。事后想想也对,他们今天生在了一个好时代里就该享福,我们当初苦,是因为生在了那个苦时代。我们苦时,不是总在想着希翼着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出生时,不再受穷受苦,餐餐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吗?还好,不仅他们,连我们也真的赶上了!
只是,唉,父母那一辈没活到今天啊!我有时不禁胡思乱想:倘若母亲现在还在,她老人家或许也会为面对菜市场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景气却老是抱怨不知该买什么好吃什么好,以及家来客人时不知该如何满足客人口味而犯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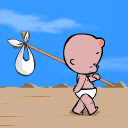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