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 缝 陈 师 傅
乐 乎
象种植农作物一样,农村缝制新衣也是有季节的。一是在春耕之前,做春夏两季的单衣,夹衣;一是在秋收后,做冬天的棉衣。
时候一到,裁缝陈师傅就来了。
陈师傅五十岁左右,胖胖的,一脸笑相,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因为他与四队五队的人家有些血缘关系,所以承包了这两队人家的新衣制作。陈师傅的缝纫铺就设在生产队的学习室,一户人家做一二天,也有做三天的,但不多。至于个别人家只做件把两件衣,那工钱就单算。
陈师傅不大乐意跟知青缝衣,说城里人挑剔,不好伺候。不过我在插队那几年,也请他做过几条长裤,几件的确凉衬衣,一件棉袄,样式不怎么样,虽土气但合身。
他的工钱具体怎么算,不太清楚,但肯定比其他的裁缝师傅便宜。农村有不少裁缝师傅落布的笑话,有一个笑话说,裁缝师傅把主人的布料铺好后,左看右看,迟迟不肯下剪。主人问怎么回事,裁缝师傅说:“难死人了,裁好了你的,就冒得我的;裁好了我的,就冒得你的,”但陈师傅从不落布,十分体谅农民的艰辛。
到他这里来量体裁衣的乡下人,无论是羞涩的新媳妇还是胆怯的小孩子,或是邋遢的男子汉,在他面前都站得规规矩矩,任陈师傅摆弄。量好尺寸问好式样后,他便吩咐几时来取衣。
陈师傅的右手已被剪刀打磨出厚厚的老茧,缝制衣服时,他抽着烟,沉思着,紧皱眉头,似乎进入了一种超然物外的创造状态。他把那些布料翻来倒去,计算着布料的幅度、长度、缩水性,算毕即在布料上喷水,喝一口喷一口,发出“卜、卜‘的声音。然后用划粉在布料上画出流畅的曲线和直线,一件衣服的轮廓就出来了。
陈师傅干活在学习室,吃饭则在做衣服的人家。裁缝师傅进门,主人家总得弄点晕菜招待。有的师傅很挑剔,如果饭菜不够档次或者味道不对口,在裁剪或缝制时便做手脚使坏。农村花钱撕布做衣服是件大事,一般人又不懂裁剪,哪敢得罪师傅呢?陈师傅却是一个难得的深明大义的人,他吃饭只好一样菜——蚕豆。春耕时节田里正好有嫩蚕豆角子出来,生产队地里的蚕豆有人看守,不让摘,但家里来了裁缝,通融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再说不少人家在自留地也种蚕豆,青黄不接之时还用它来充饥度荒呢。
陈师傅到家缝衣,不用什么晕菜上桌,有一碗蚕豆就行了,但要煮得烂烂的。大家不明白的是,蚕豆再好吃,还能好吃过肉鱼?春耕前,家家户户都还有些腊鱼腊肉,端上来,他也吃,一边吃一边埋怨主人家太过客气,还再三嘱咐下不为例。
秋天做冬衣时,要吃鱼吃肉就得到镇上或渔船上去买了。买肉很麻烦,要肉票,而农民是没有肉票的,所以主要是买鱼。买鱼要花钱,陈师傅是不同意的,你买来他也照吃不误,但事后却少收工钱。这不成了他花钱请主人家改善伙食么?人们以后干脆不再跟他客气,一碗蚕豆,一碗酱萝卜或扎辣椒,一碗豆腐,一碗鸡蛋汤就把他打发了。有时主人煮两个荷包蛋给他吃,他也要客气半天,主人会真的很生气:“你不把这两个蛋吃下去,那就是看不起我们这小户人家了。”
陈师傅做工很会为主人家着想,如果布料有多,他就会多做出件把小孩子的衣服来;如果布料有些紧张,他也会想方设法东拼西凑,在尽量不影响整体美观的前提下,交出主人定做的衣服。
今年国庆节回安乡,老乡说如今还有哪个做衣啰,都是买衣穿,样式多又便宜,后生子穿的都是流行服装,穿一年不流行就不穿了,丢给老一辈,所以老人家也有几件时髦衣服,样式虽有点过时,但穿上做客串门还是蛮客气。
我问起陈师傅,社员说他八十好几了,还在,早就不缝衣了。有时来队里走走亲戚,其他人家也争着对他尽一份心,东家请西家接的。陈师傅吃饭,蚕豆仍是必备的,但已退为陪衬,鸡、肉、鱼是主菜。他吃着主人夹在碗里的鸡大腿,发表感慨说:“哎呀,以前那个时候的蚕豆当真好吃,到底是冒下过农药化肥的,生的吃起来都有一丝甜味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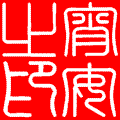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