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还有一个喜来,姓吴。为了区别张全喜的哥哥张喜来,大家喊吴喜来叫“来娃”。来娃大我三岁,属猪,是我村学历最高的人,读完了初中,他也应该是我村最有才的人。来娃长得很精神,大眼睛,双眼皮,鼻直口方,站直了也有一米八左右,可惜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就再没站直过。他就是我在本系列(一)中提到的喜发的二哥。
本来吴家这一辈,家谱规定中间的字是个“玉”字,老大就叫“玉生”,轮到来娃叫玉来,可是稀里糊涂竟叫成了喜来。据说,来娃生下来特别好看,他妈特别喜欢,就叫成了喜来,但人再穷,家谱是不能乱的,所以,上学时还叫玉来。后来他患病,妈哭得死去活来,觉得本来家里就穷,这一来,娃这一辈更完了。村里没有哪个娃读过初中,但来娃妈非让他读初中,说,娃惜嚯(方言:可怜),叫娃多读两年书,少干些活路。花点钱心安些,妈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来娃总是留着一个分头,见人很有礼貌,笑得很得体,虽然跛,却给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感觉。他口才很好,说点什么很有条理,而且滔滔不绝。来娃会拉板胡,还会唱曲。友存结婚时,他自拉自唱。板胡拉得有滋有味,他摇头晃脑,如醉如痴;唱的时候慷慨激昂,特有激情。村里人又是鼓掌,又是喊叫;我听不懂,觉得不是很好听。但板胡听着还不错。
听说,来娃参加过县里的残疾人曲艺队,曾经跟着他们在各个公社各个村演出,混碗饭吃。不久他不干了,说剩不下钱,翻山越岭的,有点吃不消。来娃和知青比较密切,他比我们学历还高,因为我们初中没有毕业。村里人一般人不会下象棋,因为认不全那几个字。来娃下象棋,居然下得还不错,敢跟知青俩干,偶尔还能赢。老实说,我们队六个男知青,没一个长过来娃。虽然我们自己未来是什么命运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来娃肯定要打一辈子光棍,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论证了。老天真是不公平------我们都这么认为。
凭良心说,不管谁当队长对来娃还是很照顾的,当然工分不高,8分5,跟妇女队长一样,比较公平。他本来也是经常跟着妇女干的,外号叫妇女二队长。哥哥经常要出去搞副业,或者去石膏窑挖石膏,或者上煤矿挖煤,或者下山到盐池担硝,总之是凭气力换些钱回来。来娃的嫂子是从山里嫁过来的,年轻,还没有孩子。一天到晚也跟着大家干活儿,穿得花枝招展,爱说爱笑爱热闹。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几个妇女只要有来娃领着干活,就拿他说笑,结过婚的女人在一块啥话都敢胡球说,来娃有时也顺势骂俏,占点小便宜,不过动真格的还没有,毕竟腿脚不利索。来娃哥哥常不在家,嫂子是女流之辈,有些事免不了让来娃帮忙。当然来娃是有求必应,自己嫂子的事不就是自己的事嘛?久而久之,那杆妇女就拿这叔嫂说笑,越说越不象话。不过这在农村是常有的事。
后来越说越玄,或是来娃半夜钻嫂子窑里去了,或是嫂子钻来娃窑里去了。甚至连来娃妈都听到了风言风语。此时的来娃妈已经五十多岁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她什么也不说,她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哥哥回来当然是听不到这些了,没有哪个人无聊到这份儿上。
事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到我离开,什么都没有发生。来娃果然打了一辈子光棍。
我08年十月回村,见到了来娃嫂子,70多岁的人,穿戴还是很干净,说起话来还是那样叽叽喳喳,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地说起来没完,真是秉性难移。
后来我找到来娃,印象中的小分头变成了短短的平头,灰头土脸,61岁,不显老。虽然不显老,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活泼,木讷得很,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住在别人家里,给人家看家。那人在外面做生意,估计是要给他一点报酬的。屋里满地都是玉米,大概是刚刚剥完皮,正准备晾晒。他让我坐,我看看没有坐的地方,就谢绝了。
过去我俩之间的接触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见了他有点激动,我以为他也会激动。可是没有,我们握了握手,他很快就松开了,脸上的表情比我想象的要平静的多。望着那熟悉的面孔,我想起那时候村里的流言蜚语,此时竟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也许那事真的有过吧?我真的希望它确实曾经发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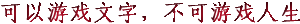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