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理解的文学,不单是文字功夫,文学的功能已经从纸媒扩展到所有领域。知青经历的几个阶段,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然后困惑、迷茫、失落、反复思考(大部分时期是后知青时代)。讲“知青文学”,实际是知青群体的一种文化,是知青生活的客观反映,更是一代人对现实的呐喊与人性的执着追求。
知青下放牵连几代人,以知青为题材的文章、作品,在80—90年代,一度成为社会文化主流。前年,电视剧《血色浪漫》将知青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剧中揉进了黄土地、西北风、青春的浪漫苦涩、知青的过去现在、人生思考等诸多元素。如果这是“知青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那应该是聚合了知青特色之大成。早期的“知青文学”基本由纸媒和口口相传体现,社会与科技进步让“知青文学”有了一席之地,比如知青网。但知青已成过去,与这一代人相关的内容,逐渐会淡化为社会的边缘题材。我想将邓贤《中国知青梦》中的一段话引用:“人的命运可以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也可以飞黄腾达数典忘祖,但是有一件东西他(她)们始终无法逾越,那就是横亘在他们心路历程上那段曲折苦难的历史,或者说由时代打在他们灵魂中那种刻骨铭心的烙印。一个人,当你直面你的同龄人,直面你曾经休戚与共生生死死的那个年代,你就永远无法逃避或者疏忽你对历史也对自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你尽可以视而不见,但是你绝对不会无动于衷。”文章感人也言之在理, 90年代初写的这篇文章,与我们今天总结知青历史,感觉比邓贤迟了一些年,今天写湖南知青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不能否认,湖知网制作的《情缘》,作为对知青史的补充,运用多种手段,以事实说话,比单纯用文字更有说服力,这方面不落后于人。2008年12月,胡总代表国家最高层,对过去几十年的所有问题,用“不折腾”做了慨括,是中国有无数要紧的问题更为急迫,就是说对过去不纠缠。但是,还有很多人想说想写,成了违莫如深的话题。你要这么做,也是一种折腾,是一种矛盾。难道不说不写?
我们还能做什么?写什么?如实记录知青自己的历史,警醒后人,我们做了,或者还不够;另一方面,知青们逐渐迈入老令,还有我们的子孙辈所处的环境,都有很多题材值得写。当前的社会热点,这码事一提就事关时政。早些天,有个当了外婆的知青朋友说:做外婆有天伦之乐,只是在家庭教育上十分困惑,经常左右为难。作为知青的我们,总希望后代人生活得比我们幸福,又往往忽视两点:对后代注重物质需求少了精神需求,被动地跟着应试教育走。其实,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误区,我们过去不单是物质条件苦,精神方面更苦,好在知青吃得苦,也有知青独特的乐观生活方式。把教育自己后代的要求和起点放低,再考虑培养生存技能,这方面也有许许多多东西可写,不能忘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还有医改,与我们戚戚相关。一言以蔽之,个人改变不了社会现状,可以保持一份平常心。知青之间的交流、活动、文章、讨论,都有无尽的题材,让知青相互帮助解惑,也扩大了“知青文学”的取材面。热门话题往往又跟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我们只能点到为止,或是绕着写,再远就越雷池。如果有更深刻更有影响力的大作,将是对当前中国社会进入转折点的一大贡献,但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出版部门发表,这叫“选庙”。早几天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女作家赫塔·米勒,又是欧美人得奖,连奥巴马都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怎么看?我不以为然。也许中国有赫塔·米勒,或是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外国庙不同于中国庙,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他(她)们在思想叛逆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想过利益和荣辱。但欧美与中国,在价值观上标准完全不同,敏感话题往往关乎国家民族,如果不择时候说,叫不识时务;过去的苦难,是全民性的苦难,说说无妨,毕竟现在自由多了,但写成文字就得负责,立字就为据。去年5.1返乡前后,我构思《背尸记》一文,是个敏感话题,亲身经历的写不好会变成诅咒谩骂,只有再现时情时景和内心的真实感受,才会增加文章的说服力。故事梗慨真实,事情起因是当时的政策造成,在描述中,将“坚决铲除资本主义尾巴!”“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放入文章,因此,这样处理不至于苍白无力。矛头也不是指向某个特定对象,目的只是反映当时的生存状况,也是将知青与农民对比。经历苦难,了解死亡,对自己有本质的提升,写的东西就会跨越个人狭隘圈子,着眼点会看到更高层面,从而把人的真善美写出来。如果单纯写自己的苦难,发泄自己的心情,就是控诉书,不是文学,或者说不是“知青文学”。
常言“幸福何其相似,不幸各有不同”。《红楼梦》给我们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写作水平叹为观止,放在篇首的“好了歌”,它的朴素唯物观对写好文章有帮助。这是我的一点体会。说到这里,我想赞美江永蒲哥的《茶铺春秋》,通篇没有自己,但一群栩栩如生的草根人物,嘻笑怒骂,活灵活现,已经超越“知青文学”题材的范畴,对知青写手选择范围有启示,对丰富知青网以及“知青文学”,都是锦上添花。我们知青中间,如果爱好文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资源,比如游客宴生,他父亲陈渠珍所著《艽野尘梦》,就是一座文学素材宝库,民族和睦,爱情、亲情,新奇,时间跨度大,朝代多更迭,可以改编成一部不错的电视剧。我之所以两次提电视剧,主要是它的受众面大。说的都是大的,非一人能为。“知青文学”只是文学的独特分支,时间会使它逐渐融合改变。一般认为,文学家不写小说,尤其长篇,就不是文学家,这是固有的看法。现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的时间节奏加快,欣赏要求不同,故而长篇看的人少些(除开专业,或者有影响的长篇)。湖知网的长篇栏目,还有书店架子上的长篇小说,即使广告造势也是叫好不叫座,恰恰短文受人青睐。如今,长篇已经远不如过去时候争相传阅的氛围。是进步还是倒退?应该是人的选择更多更自由了。说这个现象,是我知道有朋友往这方面努力,也许没有丰厚的回报,我依然报以真诚敬意。写东西费力,写好文章难,尤其年轻不再,但有不老的心态和人生阅历做资本,一定会出现更多水平高的作品。
如果能再年轻一次,我们会做许多不同的事——去读书,去创业,去玩个不知死活。想归想,年轻时的心愿不一定实现,心境也完全不同。总要活到一把年纪,自己才会了解,真正没有遗憾的人生,是在自己的那个年龄做该做的事,超越或落后,都不现实。
《中庸》说:“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我最后只说一句:我们后面还有戏,你愿意做个演员,还是观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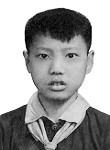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