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读老团兄的美文,我有想起当年装铁夹的情景:
铁夹子夹野猪
山上野味确实不少,常见的有野羊、野猪、刺猪、竹里猪、田猫、野兔,其中野猪、刺猪、野羊这几种野味习惯走自已的线路。区别它们的线路并不难,见到羊蹄印便是野羊的路,见到刺猪爪印,便是刺猪路,野猪的线路就更明显了,它的蹄印大,线路也宽些,那些比较小的野味都喜欢沿着它的路线上爬,所以野猪线路不但有明显的猪蹄印,还杂有田猫、竹里猪、野兔等等。
我同奶名叫元元的细伢子装过好多线路的铁夹子,所以同他还学了不少经验。别看他个小,但特别麻溜,又灵活,又聪明,讲起话来倒像个大人一样的口气。
记得,我第一次同他上山看铁夹是1966年年底。那天,我上山砍柴,正巧碰到他,听说他去看夹子,于是就跟他一起到了他装铁夹子的“引山冲”头。只见他爬上圹望了一下:“夹子被羊拖走了。”说完四周望了一下,再往下圹一跳。
他用手指着旁边的草丛:“你帮我到草丛里寻一寻。”说完自己几跳几跳下了茶籽山。
我依他的,在旁边那草丛里寻了一遍, 没发现任何东西。忽然听得茶山下“哈.....哈”的一声叫。我正琢磨着这是甚么东西叫?只听见他在茶山脚喊:“小陈,快下来,羊得了。”
我听说羊已经得到手了,兴匆匆地跳下了茶子坡,很快跑到他面前,只见他卧扑在地上,身下压着一个黄东西,我正在好奇,他抬头望着我:“快帮一帮忙。”
我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蹲下,用两手按住那黄东西,我这才看清是一只大野羊,它两只角弯钩钩的。只见元元慢慢的伸起,用右脚膝顶着野羊的肚子,那羊被顶得“哈哈”地叫。我跟着用力按住了野羊的后半身,他抽出柴刀,用刀背在羊的鼻子上上狠拍了几下。羊不再叫了,一会儿也不动弹了。
我定神仔细一看:“啊呀,这羊怎么有四只眼睛?”我好奇地问。
他笑了笑说:“羊只有两只眼珠,但有四个眼洞,前面那两个眼洞是夜眼。”原来是这么回事,羊的眼珠可以上下移动的。
我们把羊抬回他家,他用小刀很快削下了羊,将羊皮钉在火塘房的板壁上,他用菜刀将羊肉对半劈开,递给我一边肉。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能要这么多,我割一小块就有了。”
他指着板壁上钉的羊皮说:“按我们山里人的规矩,铁夹是我的,这羊皮就归我一个人,这羊是我俩共得的,你应该分得一半肉。”
我还是过意不去,执意要砍半截下来,他发火了:“难道要我元元破坏我们山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么?这种事我是不做的。”
他讲得那么诚恳,又加上他娘和他的哥哥也在旁边劝说,我犟不过他们,只得收下。
我分得那半边羊肉足足12斤,刚好快过年了,女知青都回城了,剩下我和章伢子,我俩美美地吃了几餐。还碰巧官团大队的大黄哥到我们金麦来玩,他戴着那副宽边眼镜,呷得笑哈哒。他鼓励我今后多装装夹子,可以改善生活。不用他说,从那以后,我更喜欢同元元一起上山装铁夹子了。
他最喜欢听我讲水浒传的故事和阿凡提笑话;我最爱听他讲金麦大队近些年来发生过的事情。从他口里,我了解到生产队好多人的性格和经历,我们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元元有4个铁夹子,我们分别安装在野羊路、刺猪路、田猫路、野猪路,我们夹过十多斤重的刺猪,还夹过刺猪逃跑后剩在夹子上的刺猪脚 ;夹过田猫,田猫虽然不大,但它的皮能卖2块多钱;我们夹过好多只竹里猪、野兔。
有一次,我俩到“老书冲”看夹子,刚走到核桃湾口,元元突然讲:“等一下我,我的草鞋绳断了。”
我站着等他,大约隔二分钟久我们走进核桃湾。突然,只听我们装夹子的位置“哈——”地一声叫。原来,一只羊刚好踩着了铁夹,不迟不早,正好赶上。要不是他的草鞋绳断了,我们提前看夹子,羊见到我们一定会往回转,可偏偏就有那么巧,正好赶上了。
羊拖着铁夹在核桃山里东蹿西蹿,我俩像玩“牵羊买羊”一样围着它捉。突然它被铁夹上安装的木丫棍挂住了,木丫棍挂在小树上,它急得“哈…哈…”地叫。我冲上前,像足球守门员一样,朝它身上一扑,正好把它抱住。
元元走上前来,用柴刀在它鼻子上敲了几柴刀背。,那家伙才停止叫喊,我俩乐得在核桃山哈哈大笑。
后来,我们还夹了一只穿山甲,它身上的壳卖了四块多钱。可我们就是夹不到野猪,据元元讲,他的四只夹子力量小了一点,只适合夹野羊和野猫,我们的铁夹子装在野猪线路,不是被竹里猪先踩着,就是被野猪踩过后甩在一旁。
有一晚上队上开会,有几个讨嫌的社员仗自己的出身好,说元元家是富农,她娘还是“份子”,地富份子家的铁夹子要没收。元元一听,连忙回答:“我的铁夹子早就卖给了知青小陈。”
我一听连忙接音:“他那夹子早就卖给我和老章了,老章走后这夹子就全归我了。”
那几个讨嫌的社员没办法,其实,队上的人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假的,但他们都不作声,只是捂着嘴巴笑。
我还进一步强调,:“眼看就要守野猪了,我要将夹子装到田边,保护集体的稻谷,这是革命行动。”
那几位讨嫌的社员,打冤枉主意来冒成功,便用出身来压人,我理直气壮的为元元辩护:“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出身不由已……”我用当时较流行的语言顶回了他们。再说,生产队大多数人都看不惯那两个讨嫌的人,俗话说得好:一两只蛆婆子拱磨子不翻。
我们真的那么做了,我俩将4只铁夹分两处安装在田圹较陡的野猪线路上,一来防止耕牛踩着,二来从陡坡蹿下来的野猪力量大,踩在铁夹上插得深。我们分前后装上2只铁夹,我们每天清早都去看夹子,我们没有火枪,只得各拿一把长砍刀当武器。
终于等到那一天,我俩发现野猪踩上我们装的铁夹了,野猪拖着铁夹直往下走,两边的芒灯草被踩得稀乱。我俩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田里还见不到野猪,再看田圹脚被踩得稀乱,我们又跟着跳下田圹,我们跟着脚蹄印一直追到一个沟圹边。元元伸脖子往圹下一看,大喊一声:“在这里!”
我连忙伸脖子一望,果然一头野猪躺在沟圹里。元元拾起一团田泥巴,朝沟下打去。那野猪一伸就站了起来,我又端起一大团田泥巴朝它打去,它更凶了,只往上圹爬,它还想攻击我们,但铁夹子的木丫棍挂在树枝上,它往上爬一下,又落了下去,爬一下又落了下去。
元元大声骂道:“你这畜牲,成这样子还凶什么?”他边说边跳下了沟圹,野猪把两嘴巴哒得垮垮的响,他一点不害怕,提起手中的长砍刀砍了下去,只听见野猪哇哇的叫了起来。他那一刀砍得好准,将野猪的右耳朵砍掉了半边,紧接着,他扬起长砍刀又一顿打,打得那畜牲的头血糊血海,一直打得野猪不动弹,他才停手。
我站在沟上看呆了,他那麻溜的手脚,敏捷的动作,真令人佩服!他将野猪翻了一下边:“快下来抬,迟了怕碰上人。”
我这才明白过来,向周围望了一眼,没有见人来。我俩将野猪连扯带推弄上了沟圹。他砍了一根红藤将猪脚交叉捆好,我砍了一根小杉树做杠子,我俩摇摇晃晃的抬上了肩。
野猪虽然不大,加上那两只铁夹挂在一起,走起来还蛮吃力.他边走还边讲:“我第一刀,砍断了它的耳朵,剩下我都是用刀背打,要全用刀口砍,会砍得稀巴烂。”
我连声说到:“你经验足,手脚好快喔!”
一路上,他还讲了几年前他守野猪时,发现一头野猪婆引着五只猪崽在田里,他不顾一切硬砍死了一头小猪崽。他还说“过难关”(苦日子)的那年,队上的杨政金发了一财,他捡得一头被老虎咬死的大野猪,足足有300斤,那野猪只被老虎吃了一腿肉,野猪油都煎得有30多斤。
不知不觉我俩抬着野猪进了寨子,正巧碰上在大队副业厂做木工的杨木匠,他硬要买去给副业厂人打平伙,我们俩考虑自己也吃不了那么多,于是便用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们,野猪虽然不大,但我俩一人还是分得8块多钱。
山里人夹野猪夹得多,但大多数都是拖着夹子跑好远才用火枪打死。铁夹夹野猪,给枪打野猪提供了优越条件。按山里人规矩,铁夹子夹的野猪被人打死,如果铁夹的主人在场,也只多分猪头或者猪脚,如果铁夹主人当时没在场,最多退还铁夹,客气的话可分上几斤肉。
野猪瘦肉多,肥肉少,大野猪的皮约半寸厚,将那厚野猪皮用鼎锅炖上半天,那皮炖得成肉膏,咬一口又细发,又软心,唉呀!真是绝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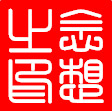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