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 释
文/新生
在我人生的五十八年漫长历程中,曾经历了好几次较大的政治风波,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其中有一次“灾难”险些宣判了我政治上的死刑。今回想起来,一直心有余悸。
一九六八年秋收过后,时年十八岁的我被“下放”地——湖南省衡山县松柏公社晓岚八队队委会指派到该县新桥水库当民工。从早到晚从事着挑土、挖土或打土车子等繁重的强体力劳动。有一天下午,我们大队民兵连指导员、党支部副书记老符叫我到工程指挥部去领炸药和雷管,准备放石炮。我便遵命去了仓库。到那里一看,恰好保管员是我的艺友小刘。他时任技术员兼保管员,我们原是“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衡阳司令部南岳支队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队员,同时还是原“衡山县南岳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主要成员。他乡遇故友,顿感格外亲。几年未见面的刘与我于是又拉起了家常,叙旧怀乡。老朋友相聚,总有许多说不完的知心话。临别时分,小刘叫我常到他那里去玩。我领好炸药和雷管之后,便去复命。
后来,我和小刘几乎每晚都呆在一起聊天,友情与日俱增。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我们队上的“政治队长”老赵受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周的派遣,到工地上来通知我回队上去劳动。我问老赵是什么原因,他告诉我说是公社要举行学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汇演”,叫我回去排节目,因我当年参加了“晓岚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故必须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安排。我问老赵什么时候动身,他说三天之内即要集中排练。于是,我即刻去工棚收拾东西,老赵则去和大队民兵连交涉抽我回去之事。并相约吃了午饭后一起回队。赵便在“连部”休息,我则准备与刘去道别。正在这时,小刘不请自到。见此情形,刘问我要到哪里去,我就将此事告诉了他。恰在这时,赵进来了。我连忙将他们相互作了介绍。赵得知刘的身份之后,开门见山地向小刘要炸药和雷管。我俩感到很吃惊,刚认识的人就向他要东西,老赵也太不懂味了。小刘也不好不给,只是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张扬,以免麻烦。赵便拍着胸脯向小刘作了保证。记得赵当时是这样说的:“刘师傅,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小唐队上的政治队长,我向你要炸药和雷管只是回去炸鱼吃,决不会出事的。万一有人追查起来,也决不会连累你,更不会牵连小唐。你就放一万个心吧,绝不会有任何麻烦的!”小刘见老赵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不好拒绝他。便带他到仓库里私下里给赵五筒(每筒一市斤)炸药和五个雷管,随即回到了我们的工棚内。午饭后,我向小刘道了别,与老赵一起踏上了回队的路。
回队后,我每晚在大队部排京剧《智取威虎山》。我的任务是负责乐队伴奏,拉京胡兼教唱腔。早把炸药雷管之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谁知几天之后,赵队长在晓岚港炸鱼时,因他一人独自享用所炸之鱼,不肯分一条给任何人,引起了社员们的不满;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大家议论纷纷。这事很快被公社武装部刘部长知道了。当即对此事进行了全方位调查。我知道后,顿感不妙,一下子懵了。心想大祸就要临头了,真是悔不当初。
当时,刘部长把“炸鱼事件”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又一新动向”来狠抓猛打。不过,赵暂时还没把我与小刘供出来,我也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半个月之后,公社如期举行“样板戏汇演月”。全社二十多个大队每晚由一个大队进行专场演出,如火如荼,盛况空前。轮到晓岚宣传队演出的那晚,我们正在演出《智取威虎山》第四场“深山问苦”一场时,“常宝”高唱:“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一段唱腔,我正在舞台右侧与乐队的人全神贯注地伴奏时,突然从舞台后面窜出八个穿着无领章帽徽的军装、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小将,不由分说,便将我当场用手铐铐住,押于舞台正前方。这时候,刘部长威风凛凛地走到正前方,对着台下观众大声宣布:“贫下中农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广大下乡知识青年们!现在,本部长代表松柏公社革委会向大家通报一个大快人心的喜事:暗藏在晓岚八队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份子、大特务唐未之的狗崽子——小特务唐容颐,因对党和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不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还企图炸毁我人民公社;真是狗胆包天,用心何其毒也!孰不可忍!生不可忍!他娘的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新桥水库工程指挥部我家门那里偷盗五筒炸药和五个雷管,送给晓岚八队政治队长老赵,企图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真是罪恶滔天!罪该万死!罪不容赦!现在,本部长命令:把唐容颐押下台去!取消他文艺宣传队队员资格;同时,从即日起,清除出知青队伍!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另外,本部长还要向晓岚大队党支部、革委会提出严正警告:你们敌我不分,竟公然允许阶级敌人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这种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更是不能原谅的!也是不可饶恕的!现在,我宣布:改组晓岚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周正坤同志停职检查!下面,演出继续开始!”于是,几个红卫兵争先恐后地推搡着把我押下了舞台,随即把我关押在一间又潮湿又昏暗又脏又臭的仓库里。由于我的无端被抓,至使演出因无人接替我拉京胡而只好停演。那些来看戏的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后来,小刘也因此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就这样,我被关押了二十多天。每在只有早、晚两次由公社伙房大师傅各送一钵三两米的饭加一点儿萝卜、白菜之类的蔬菜,从未开过荤。睡的是地铺;没有换洗衣服鞋袜,也没有手帕牙刷牙膏。连上厕所也得报告,由看守人员恩准后再在他的注视下匆匆解决,生怕我越狱逃跑。
在这期间,刘等一伙先后多次把我提审、罚跪、大小会议严批狠斗、押送游乡等。到使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我也从此而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政治运动员”和“现行反革命”。一时间该社对我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由于我是代人受过,为使与我一起被驱逐下乡的母亲及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不受牵连,我一直守口如瓶,未透露半点事实真相。刘等一伙便对我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他们一直未审问出什么名堂来,故也定不了我的罪。其时,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们不准我的家人来探视,边东西也不准送,怕我搞串供。我母亲当时也不知道我被抓之事,是好心的村民告诉她之后才知道这事的。我母亲成天唉声叹气,黯然神伤,寝食不安,每天以泪洗面。真是祸不单行,我父亲一直被关押在南岳建筑公司(后也被驱逐下乡),如今我又被关押近一个月,真是苦不堪言,有冤无处申。
由于营养不良,我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简直被折磨成了一个叫花子。可刘等一伙还是不放过我,一直把我当作“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进行无休止地批斗。队上知情的贫下中农也愤愤不平,他们私下里在为我求情说理。以生产队长张彦丸为首的全队二十五户户主出面,联名写了一封“保释书”,内容大体如下:(此件后存松柏公社革委会敌伪档案中)
松柏公社革委会并武装部:
兹有我队社员唐容颐,系本县南岳镇下放青年,现年十八岁。受我队指派在新桥修水库时,私下里与人合伙骗领了五筒炸药、五个雷管,交由我队政治队长赵聚培拿回家后,在晓岚港炸鱼一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是为过错。但他并非要炸毁人民公社,也没从事任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勾当,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此事事出有因。因此,我队全体社员代表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唐是可以改造和教育好的青年。现特呈具“保释书”一封,请求公社立即将其释放回队,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在劳动中接受再教育。
望予批准为盼!
衡山县松柏公社晓岚大队第八生产队(公章)
全体社员
1968年12月XX日
附:名单如后(略)
这封倾注了贫下中农深情厚意的“保释书”上还郑重其事地签了二十多个社员姓名,且分别加盖了私章,无私章的户主则按了手印。就是这封“保释书”救了我一命。记得那天下午大约三点多钟的时候,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由张队长带队,男妇老少一行还有我母亲及弟妹共约四十余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公社机关大院。他们打听到关押我的地方后,张队长喊开了门。母亲见我这副骨瘦如柴的模样,顿时伤心地流下了几行辛酸的热泪。大队的秘书老符的母亲符奶奶端来了一碗白米饭,菜是荷包蛋炒辣椒,还有白菜,她把饭递上来,说:“真是作孽啊!容颐,看你饿成这样,真叫人心痛!来,你快把这碗饭吃了吧!”我接过饭碗,还没开口,眼泪就止不住地往饭碗里面流,队长夫人老杨和我母亲在一旁沫泪。我哽咽着说:“谢谢符奶奶!”继而喊了句“妈妈!”就哭了起来。俗话说:“男人有泪不轻弹。”没有经历过这种磨难的人是根本体会不到这话的含义的。
这时候,张队长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小唐,我们大家是来保你出去的。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保释书”交给我看。我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了张队长。我说:“谢谢张队长!谢谢乡亲们!只怕刘部长不会放过我,反倒是连累了大家,你们都请回去吧!”
张队长说:“你放心!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分得清。你这么年青,绝对不是什么“小特务”,更不是什么反革命份子,我们一定尽全力保你出去。如果刘部长不同意放你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走了!都在这里静坐示威,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不怕他开除我的锄头把。小唐,你快吃饭,我们找刘部长去了!”说完,他们大都找刘去了。只有我母亲和符奶奶、队长夫人等妇女仍然守候着我。符奶奶又催我快吃饭。于是,我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饭,一边流泪,眼泪和着饭菜一并吃进了肚子里。这是我被关押二十多天来吃得最好、最饱又最香的一顿饭。
没过多久,张等众乡亲又来到“牢房”里,对我说:“我们终于成功的保释了你。”我说:“谢谢!”话没说完,又哭了起来。张队长说:“别哭!你要高兴才对。刘部长迫于压力,只得勉强地同意放了你。条件是由队上监督管制你劳动生产。走!我们回家去。”于是,我便跟随张等一行四十余人走出这个伤心之地,回到了队主,回到了家里——我的第二个故乡晓岚港。
这事虽已过去了三十九个年头,但一直令我难以忘怀,感动不已!当年,若不是那些纯朴善良而又可亲可敬的贫下中农集体请愿,写下这封精心制作的“保释书”去公社保我出狱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日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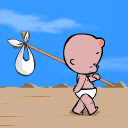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