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那时的山水那时的人(上)
分插到工区内各老职工队,是我们踏入社会生活的第二课。少了一些学生的浪漫、空想,多了一些务实、谋生的脚踏实地;从比较单纯、单一的学生关系转换到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层的融合。于是乎,无论是生活方式、习惯,还是思维方法,甚至言谈举止,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以至于影响了我们一生。当然,知青们所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文明习惯,也似一缕清风吹过古老、传统的山村。
这次回江永,无疑是一场怀旧之旅,我们想到我们曾经去过的每一个村子,尽可能多地见到我们想见的人,我们想探究一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第一站就到了马鹿头村。一下车,只听到一片叫 “枇杷露”和“周兰”的声音,她们的人缘关系曾是太好了,一下子同时被好几位农妇拖住,要往自己家拖去。1963年周 兰还是一位不到十五岁的小姑娘时就下到回龙圩农场,她先后在马鹿头、石头水、田美队干过,从马鹿头工区调出后,又到新思工区好几个队工作过。在马鹿头村,她吃苦耐劳,办起了养猪场,被猪潲烫伤了还坚持不休息,被誉为“铁姑娘”,团员青年选她为工区团委书记。文革初期,她父亲受到冲击,受牵连工作组荒唐地把她也打成“反党分子”,组织团员批斗她。批斗会的第二天一早,她照样按时出工,村上的伯娘、婶娘、小姐妹们仍如往常一样和她打招呼。她说:“团委书记我可以不当,你总不能剥夺我出工的权力。”在村妇们的呵护和关爱下,她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岁月。回城后我们才知道周兰是我省一位老国学家周仁济先生的女儿。周先生蹲牛棚时,他不知道他的爱女也和他一样在受苦受难。女儿一直都没有告诉他。这次回马鹿头,听到农妇用土话或官话招呼周兰的声音,显得格外甜润动听。“兰”字本是一个平声字,在浓浓乡情乡音的呼唤中却成了一个仄声字,拖长、扬高,表达着一种由衷的欢喜,这也是一生研究训诂学和古音韵学的周老先生取名之初始料未及的吧。听何裕建介绍,江永女书的读音就是江永土话的读音,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从来也没有听到把一个人的名字叫得这样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以致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也学着用这种乡情的腔调招呼她了。
我们首先去了何裕建家,拜会了他的父母,一年不见,精神依旧癯铄,提起去年在长沙的会面,格外兴奋。他母亲拿出西瓜和橘子招待我们,一再说橘子虽然青色,但味道还好,是一种早熟品种,我们剥开一尝,果然没有青涩味,酸甜酸甜。他父亲拿出一本相册,是他们老两口在北京和美国与儿子一家的照片,我们第一次从照片上见到了他们的媳妇。我打量着他们的家,一个普通的江永农家家居,却打扫得很干净、摆设得很整齐,门楣上画着“竹苞松茂”的字画,不失农家本色又透出几分“诗书传家久”的蕴味。趁着她们交谈甚欢,我和谢周迪、陈迎楷拿着相机满村子走起来。当年工区盖的粮仓依然四平八稳立在路口;初下乡口馋常光临的商店却人去屋空、风光不再;村后的山上冻死的老树兀立在苍翠之上,使人可以想见去年冰灾肆虐造成危害的程度,令人感叹唏嘘不已;当年我们知青居住过的房子地基上已盖起了新屋,村子里不少房宇都空了,村上人告诉我们,房主已在县城里或公路边盖起了新房,过起了城镇化的新生活。
离开马鹿头村后,我们去石头水村。1968年我们离开向阳队后,知青小组就落户在石头水;这次来江永的八位知青中有四位在石头水呆过,所以除上阳峒外,我们也格外钟情石头水。
我们在石头水的几年中,正是文化革命方兴未艾、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年月,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受到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异常紧张,当时的生活也格外的艰苦。坐在去石头水的车上,我们聊起了当时的两个小段子。第一个段子是朱狄模仿当年老队长用土话吆喝出工的段子:“ton gail I nienie huo molutu hefui heidahui hawu yueli!“翻成官话就是:“明天早晨,个个去马鹿头开会,开完会进屋吃早饭!”朱狄尖着嗓子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大笑之余,感到当时开会确实常常是我们早晨梦醒来的第一桩事。另一个段子是谢周迪讲的,讲石头水队上开会,欢迎场部来的工宣队,会场里这边响起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如森林般拳头举起;那边又回应:“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顿时卷起一片掌声。“仔细一看,两边领呼口号的竟都是知识青年,一个是插队的知青,另一个是刚调到联合加工厂的知青。”谢周迪尖刻地说:“不知怎地,两位知青都成了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了!”
初到石头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住在荒废的祠堂里,四面通风,晚上蚊虫叮咬;菜土才开垦洒种,没有菜吃;最不能适应的还是老队的作息时间,拖得长,不讲劳动效率。最记得的就是石头水除早工外,还有早早工,晚工外还要出晚晚工,听说是为了照顾那些带奶崽的农妇才作此安排。春插时,每天都要在外面工作十七八个钟头,摸黑进屋,胡乱扒几口饭,有时连脚都没洗,倒在床边,就酣然入睡了。
至今铭刻在我脑海中的一幅画面就是我们在石头水出晚晚工扯秧时的情景。淫淫春雨下个不断气,我们知青组的人披着蓑衣在扯秧,田埂上,汪淮海提着一个铁丝网兜,兜里点燃着枞膏火在给我们照明,四面的群山笼在黝黑的天幕下,整个世界只留有这一星点光芒。春寒料峭,我们双脚浸在水中感到丝丝寒意袭来,加快了手上的动作;而站在岸上裹缩在塑料雨衣中的汪淮海却在风中瑟瑟发抖。听谢周迪说,小汪最近犯眼病,每天敷药还不见好,弄不好会双目失明。我们都急着叫她早点回去,她却执意陪着恋人谢周迪坚持到完工。那真是我们在农村最艰难的时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到省展览馆参观汪淮海等四位省城女画家画展时,我发现,和其他女画家不同的是,汪淮海画的全部是工笔花卉,她尝试着用不同的材质作底材,运用不同的颜料,展示各种不同的花卉,在熹微的晨光中、在黄昏暮色的掩映下,甚至在朦胧月色的熏染时的摇曳多姿。我细细的感知着光线的折射、光谱的起伏,色彩的变化,读她的画,你能感到画主的心声如一首奏鸣曲,从画中汨汨流出,你会由衷地感叹:生活是多么美好!那一刻,我站在她的画幅前,感到深深的震撼,从风中瑟瑟发抖的知青到省城小有名气的女画家,她一直在用她的眼睛和心灵,锲而不舍地追索着美,只有我们才知道她经历过怎样的艰难险阻、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才攀爬上艺术的一座座峰峦!
在石头水队,我们知青组开始了艰苦的第二次创业。毕竟,我们在向阳队已经受了生命中的第一次磨练,当初的毛头小子已长成壮汉、淑女已蜕变成铁姑娘,犁耙功夫、轧茶籽、烧石灰不在话下,泥工、木工全在行,谢周迪等几位男知青编织的篾篓也像模像样了。我们倒树锯板折旧屋,铺楼板砌砖墙加隔断,改善了住房条件;没有菜吃,我们采取去县城买一点,老职工送了一些,再就是抓紧蔬菜早熟品种的培植等办法解决。收工的路上,我们到两边的山上挖笋子、翻石头下的石耳,雨后天晴我们到树林的茅草里翻寻蘑菇,下河捉鱼捉虾抓螃蟹,日子一天天好起来,逢到知青伙伴串门,我们也能摆出像样的菜肴,就着“红薯烧”和米酒,小酌一番。我们用不吝付出的劳力、熟练的劳动技能,心贴心的诚恳态度赢得了老职工的赞誉,那些妖魔化知青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和农民的关系自然就得到修复。对拥有应付各种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我们充满着自信。在去石头水的车上,我们怀念起当年同一个饭锅里吃饭、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 “插友”,他们是:曾澍林、李梅琳夫妇,吴晋、罗先恬夫妇,还有朱狄。
汽车停在路边,我们下车,远远看到石头水在古树的掩映下依然庄重、古朴,村前池塘边一棵古树下,一块嘉庆年间的古碑赫然映入眼中。几年前,在唐志龙邀约的一次聚会时,《茫茫东欧路》的作者凌一鸣曾说起过这块碑记,说是有很厚重的文化底蕴,我还曾自责:在石头水多年,竟然没注意过有这样一块碑。没想到,这一来全不费功夫,许是村民知道了这块碑的价值,将周围修整,古碑才露面于天下。如此看来,石头水无疑是一个明清古村了,我们一行人少不了争先恐后地在古树下与碑合影留念。
进到古村,来到门楼,和我们打招呼的人多了起来,我发现,凡四十五岁以上的村民,差不多都还能叫出我们的名字或外号。我们忙着从一座门楼走到另一座门楼,从一户民居走入另一户民居,问候着多年不曾谋面的老少爷们、伯娘伯婶,乡亲们也围着打招呼,我们应接不暇。
最令人称奇的是光旺的老母亲,九十八岁了,竟然清晰地叫出我的名字,那一刻我惊愕得心都要跳出口来,我紧紧的握住她枯槁的双手,看着她布满岁月沧桑犁沟般的脸面,凹陷下去的眼窝盈满老迈昏花的泪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幅名画《父亲》,想起了阎维文《母亲》和刘和刚《我的父亲》中的歌词,手不禁抖动起来。
谢周迪和陈迎楷用相机从不同角度定格下这难忘的画面,这两张一组的照片,将永远留存在我人生的相册中。
按照我们长沙人的规矩,百岁老人称为“人瑞”,晚辈应敬上红包,仓促间我忙从口袋中取出礼金,双手恭恭敬敬地奉上,祝福期颐之寿,健康无忧。
为什么石头水人这么久了还记得我的名字,我想,这可能与我当年在队上办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有关。1970年冬,我将队上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排练了一个《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场景歌舞”。
早在中学时,我们就读过一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课文中,那蜿蜒在山路上的红军的火把给我留下了印象;到江永后我曾听说,红军长征过都庞岭,经过道县,有一支小队伍到了江永,,还在现江永一中学一棵大树下刻下标语;我突发奇想,以山里人照明常用的枞膏火把作为道具,把当年红军举火把行军这一深具历史内涵和象征意义又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情景再现出来。为了保证音响效果,我还请出知青组成的乐队伴奏。
演出取得极大成功,当村民们看到村上那些熟识的奶崽女娃,如今别着红领章,挂着小马枪,举着枞膏火把,在宏大的乐曲声中冲出亮相,当看到红军队伍在晒谷坪上变换着队型,表现着过都庞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时全都沸腾了,石头水的宣传队出名了,石头水人在外村人面前昂起了头,我们知青自然成了队上的有功之臣。
不久,工区抽调我到工区文艺宣传队任编导,《红军不怕远征难》也被工区移植去成了保留节目。离开石头水的那段日子,石头水人都不理我了,他们认为我抛弃、背叛了他们,偶尔在马鹿头遇见,相互尴尬地一笑,使我难受了许久。
几十年后,石头水人还是记住了我,他们还记得宣传队和那原始简陋的演出。一进村,一位农妇就跟着我们,介绍说自己当年是宣传队的,我只觉得面熟叫不出名字,倒是汪淮海还记得,叫则珠。她一直陪着我们,走遍了村子 的角落,主动带路帮我们找到当年夏旱时挑水的古井,映着古井清澈透底、永不干涸的泉水,她留下了和知青的合影。
在石头水,我们走进了花宜的家。花宜和我们知青关系很密切,我们即算离开了石头水,仍关注着花宜和她的家庭。
1968年我们初到石头水的一天中午,一位脸面黝黑、颧骨略高的农妇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她自我介绍说,她叫花宜,原是广东新会人,被人拐卖到了这里,几年前她娘家人找到了这里,她也带着大崽回老家一趟,她老家一个弟弟,好像还当了一个派出所所长。在广东住了十多天,她还是回来了,因为她在这边已经生儿育女了。“走不脱了!”她抹着眼泪细声地哀叹着。许是看到我们也是外来人,她本能地把我们引为同路人,话特别多,她说,冬成就是她老公,生产队长,我们有什么困难事,她可以去说一说。见我们没有什么菜吃,她回屋端了一大碗坛子菜来。她的身世和善良的心性顿时博得我们的好感,能认识队长的婆娘,我们也很高兴。几位女知青不几天就和她亲密无间,出工收工,一路同行了。
花宜有一男一女,女崽清秀,已出工挣工分了;男娃瘦高,一双大眼睛,和冬成蛮挂相的,还在读书,小男孩蛮调皮的,我们叫他“跳跳”。办宣传队时,我把两姐弟都吸收了进来。
在女知青中流传着一个“跳跳”的弟弟出生的“段子”。出早工的时候,花宜还典着大肚子和知青们一起去收稻草,上午出工时却没见到人。有人说,花宜喊肚子痛,可能是去生小娃子去了。到了太阳下山收工路过池塘边,暮霭中可看见花宜正蹲在石台阶上洗屎尿布。知青们和她打招呼,她仰起苍白瘦削的脸,喜悦地宣告,又生了一个“小跳跳”。
我们看着“小跳跳”一天天地长大,也是一双溜圆溜圆的大眼睛,肥嘟嘟的小脚丫,满地里跑了去,我们逗他玩,他一点也不认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不到一岁时因为发高烧却夭折了,而且是死在我们送他去农场医院的路上,至今我们也搞不懂到底是得了什么急症。
当我们失望地返回石头水时,花宜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从我们住屋的楼板中抽了几块下来,钉了一个小棺材,把“小跳跳”埋葬在村后的竹园里。整个过程里,冬成都是默默不作声地操办着,见我们忙出忙进、忙上忙下,夜又深了,他就杀了一条嫩狗,硬是拖我们进屋吃。我们看着热气腾腾的锅子,个个心里都十分难受,谁也抻不下筷子,胡乱扒了几口饭,回知青屋睡觉去了。
我离开石头水后,听说花宜又生了一个女崽。
1985年,我回江永,从挂牌山沿古驿道直上石头水,落脚在冬成家。花宜的儿子“跳跳”一年前从深圳沙头角当兵回来,买了一部汽车跑运输,家里的日子有了起色。小伙子高高大大,满口新名词,除了眼睛大大的像他父亲外,其他的,一点也不像他父亲了。
2009年,我们又跨进了花宜家,已不是原来的老屋了,按照现在农家的格局砌了新砖房。大女儿嫁了好人家,生活幸福美满;儿子有了大出息,在外面闯世界,买了新房,他们都要接老母亲去住,花宜说:”我不去,我还是在石头水好。”现在,花宜和小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一个特老实憨厚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我们交谈,花宜介绍说:“这是我女婿”。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外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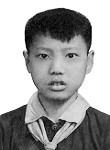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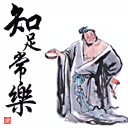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