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年前我们上山下乡 (之一)
二零零八年,七月流火,闷热了一晌的天气,恰在这时有了一丝凉意。天空上的乌云翻滚,瞬时便倒下一阵瓢泼的雨水,可转眼间又是晴空万里。天气总是在这样的快速变化中让人捉摸不定,内心的情绪就象此刻的天气变得更加烦燥。
我和冯约定今年想方设法去一趟原先当知青时插队落户的地方去看一看。时间一晃都四十年了,那儿的一切,过去我们留存下的一些纪念与记忆还在吗?那里的一些熟悉的人物与事情都有哪些变化?魂牵梦绕的积淀在心里,一年又一年,沉甸甸的。
四十年前我们都还是一群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而今垂垂老矣。想当初我们惶惶然如丧家犬一般逃离了农村,在城市里奋斗拼博挣扎,没有功成名就,没有腰缠万贯,没有衣锦还乡,但我们都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多少次在梦里回到知青年代,回到当初下放的地方,梦到艰苦的劳动,生活,苦中作乐的游戏,嘻闹与种种欢快;梦到尽其所能帮助和照顾自己的朴实的乡民,也梦到一些荒唐,愚昧,毁弃身心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梦到曾经有过的漫长岁月的磨难与无奈的等待。
四十年来,有过多次回返农村去看一看的机会。政府的组织,朋友的邀请,出差与旅游时路过等,但都被有意或者无意的推辞和拒绝掉。一直在心底认为,对于我们而言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直到近几年,年龄变老,心态也莫名其妙的起了一些变化,怀旧和感恩的情绪象野草般的滋生,平和善良的心境沉淀了许多生命之中的不满与怨恨。过去的一切总是非常自然的柔和的洗荡着心灵,多少朴实的生活场景与画面,固执的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成为一种迫切的,想方设法在今生今世要完成的愿望。
毛主席想停止文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多,全国人民从上往下都感觉无所适从,感觉着烦闷,不知这场混乱的革命究竟要向何处发展?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五大红卫兵司令,对他们进行严历的指责,说:“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并决定向全国大中专院校派驻工农兵宣传队。过去是放虎出山,现在准备收虎入笼,实际上也是发出准备结束文革运动的一种信号。
因为文革,已经有三届大中专毕业生未能分配。如何安排这几千万学生?确实成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好在不泛以革命的名义,“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句句振聋发聩的口号。一个发疯的时代致使每一个人都是疯狂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当初的潮流所裹侠,由不得你细细思量考虑。
且不说一匹正疯狂奔驰的野马——“文革运动”,能否被一双巨人的手所拦截下来。反正所有的学生都回到了学校,开始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一些“反动派,黑四类或五类分子,野心家,小混混,包括昔日的造反派和革命闯将”都纷纷被关进了监狱。当初这场运动的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经过了一系列触及灵魂与皮肉的教育后,又开始了一一平反,走马上任,官复原职。原以为社会从此太平,多少人会山呼万岁,感恩载德。树欲静而风不止,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开始了上山下乡,老三届首当其冲,原来是四个面向:“下农村,进工厂,参军,升学”,我因为学习成绩好,身体欠差,连续三榜推荐为升学。我一次二次,几次三番地去市中心广场送别下乡的同学,暗暗庆兴自己能够被留下来。
第一次送别的场面特别隆重,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几乎倾城出动,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送别仪式达俩个多小时之久,上台发言的代表一个又一个,慷慨激昂,热血澎湃。送行的车子排成一条条长龙。道别,珍重,嘱咐的话语说了一遍又一遍。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四个面向改成一个面向,所有的毕业学生全部上山下乡。当我接到学校下乡的通知,全班同学只剩下最后三位,我和另二个已经在工厂上班很久的学生。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很平静的接受了现实与命运的安排。
那个时代,物质特别贫乏,凭着一张下乡的光荣证才买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如肥皂,毛巾,手电筒等,其实也没有钱去添置其它东西。
我们下乡的那一天,出乎预料的冷清,没有送行的朋友与亲属,天一直下着绵绵的小雨,车窗外刮着凛冽的北风,这一切倒应和着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境,对未来生活的茫然与担忧。车开行了很久,除了粼粼的车轮声,只有一遍沉默,难耐的静默,终于被一阵慢慢而起的哭泣的声音所代替。 二,
农村贫困的现实、知青的教育。欢乐与忧愁
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贫困在想象之中。解放已经近二十年,农村的贫困仍然到如此的程度,确实出乎意料。在知青将要下放的地方——公社组织起一支稀稀落落的欢迎队伍,不管年青老少一律穿着单薄的自家纺制的青黑色的土布纱衣服,大都打着赤脚,着一条单裤,有的小孩甚至赤裸着双腿,站在寒风冷嗦嗦的村口迎接着我们,鼻涕和疑结的水气在满是泥土灰尘的脸面上,看不出有多么喜悦,更多的是惊讶和好奇。
一眼望去,除了公社附近有几栋二层高的新的红砖楼房外,大都是简陋的泥土屋和木板楼房,当然也有一些古老的青砖瓦屋,年代久远,已呈破败之象。尤其是每家每间房子的窗户都非常小,好像是有意要把阳光挡住,房子里一天到晚,一年四季几乎都看不到阳光,潮湿阴暗,散发出种种霉味来。当地人似乎已经习惯,倒是知青,几年居住下来,大都因此而患有风湿病痛。后来得知,此种习惯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老百姓为对付土匪与白军的骚挠而为之,主要是让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
我们下放的地方是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率领红军闹革命的活动区域,当时涂写的标语随处可见,山上挖的战壕,垒起的石壁,石壁上的弹孔都依然还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参加革命的人,有的成为烈士,有的成为今日的将军,如海军司令刘道生,军区司令有段苏权,段焕竟等。
大队部的村口有一棵大樟树,当年的红军战士在下面集合出征,一些红军战士牺牲后也被埋葬在树下面,我们下乡后第一次阶级斗争教育,就在这棵大樟树下面,由大队的贫协主席给我们讲当年的故事。他文化不高,讲话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他的身材很高,佝偻着腰,满脸的沧桑,平时手挽着一只箢萁在路途村口检拾狗粪。原来大革命时期他曾是谭震林的警卫,后来升为红军排长,长征时在湘江战斗中因受伤后被打散。
村口的大樟树是土地革命的象征,今天的很多事情也仍旧不断的,在它的见证下发生。公社的武装部长带着民兵在它下面拷问和吊打四类分子和所谓的反革命,如,有的因讲错一句话,有的把印有毛主席的语录和像章的报纸去贴窗户,有的是别人随意的检举和揭发,甚至是恶意的报复等等。
我们下乡的这几年,在大樟树下面,逢场赶墟,相聚话别,喜笑作乐,畅想未来,互相鼓励,吐诉衷情,舔舐伤口等。它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每一步,它在每个知青的记忆中都有着深刻的印像。四十年后,我们直奔乡下,遍寻它的影踪而不见,内心的惆怅与落寞可想而知。
下乡后的第一年,应该说欢乐喜悦大于忧愁,少年滋味不知愁,所有的知青几乎都是同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彼此都很熟悉,一个公社又有各种各样的下放人员,如,干部,教师,演员,大学生,社会闲散人员等。劳动之余,在一起相聚,思想交流非常方便,也很活跃,都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在第一年,每月都有几元钱的基本的生活补助费,吃饭不成问题一切好办。
一些年青的下放干部和大学生每月能发四十多元的工资,却不用下田劳动,整天干着一些轻微的活儿,如写写画画的宣传活动,让知青们羡慕的很。他们成为我们知青‘打秋风与敲诈‘的对像,他们也乐意请客,常常使唤我们在他们之间去跑腿,或传递一些爱情的信件等。一年后,所有的大学生都回到了城市,他们用国家发放的工资买到了乡下很多便宜的东西,也收获了爱情和友谊。
我们留在农村继续着遥遥无期的艰苦地劳动,第二年开始我们一无所有,与当地的农民一样要完全靠自己,自食其力的用劳动去挣回我们自己的口粮了,我们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也很无奈。
就是一个本地的强劳力也几乎养活不了自己的,一天的劳动工值不过几角钱,粮食产量非常低,二季的水稻产量每亩总共不会超过四五百斤。农民依照着毛主席的教导: “忙时吃干饭,闲时吃稀饭,夹以红薯等杂粮。”我们知青的劳动工分最多六、七分,不管多么的强壮,努力,吃苦耐劳。记得在我们知青去修水库时,一样的劳动任务与强度,工分值就是没有农民高,女知青在这方面就更少。每一个知青要在乡下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都需要家庭的帮助与接济,家庭困难的知青比比皆是,真不知如何度过这今后的难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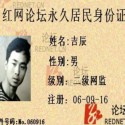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