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我还没有搬家,我玩耍的世界除了门前屋后的树丛水沟之外,就是那林木茂密的后山了。
我沿着熟悉的小径溜到后山树阴下的草丛中专心致志地捉了大半个下午的蚂蚱,一直干到日头归西。随着光线的渐渐转暗,一种原始的莫名的恐惧从我幼小的心头升起,我中断了工作,收拾好战利品-----几只可怜兮兮的折断了大腿的麻褐色的能蹦善飞的山蚱蜢,我要逮的就是它们。对于那种手到擒来的青绿色的脑袋尖尖的笨拙的草蚂蚱,我还真不屑出手。----一溜烟地,我跑回了家。
一脚踏进阴凉的家门,我的隐隐的不安与恐惧顿时烟消云散,那种涌上心头的莫以名状的安全感带给年仅5岁的幼童的感觉,与多年后明白的在外云游的浪子归家时的感触真还没有多大不同。那是温馨、安宁、松弛、慵懒的感觉,象是寒冷的冬夜泡过热腾腾的温泉浴后的感觉,象是瞌睡虫坠住了上眼皮,一心想钻热被窝的感觉。
我跑进妈妈的房间,向妈妈炫耀一下午的战绩,房间里是熟悉的小妹妹的尿布散发出的淡淡尿味以及她和妈妈身上的奶腥味。我夸张地讲叙捕捉山蚂蚱的不易:要尽量放轻脚步,不能让影子落到它的身上,扑过去要迅猛,还要算准提前量,对准它逃逸方向的前面一点下手,即使如此这般,也还每每落空。妈妈微笑着静静的听着,并不打断我,只是仔细打量着面前的野了半天的平安归来的不安分的儿子,她伸出右手,摘去沾在我头顶的一根枯草,顺手拍打了两下我肚皮前面的灰尘,继续听我断断续续的描绘。我告诉妈妈,一只巨大的蜻蜓落在那里,被我一把紧紧抱住它那又粗又长的尾巴,还被它拖得离了地!“后来呢?”依旧微笑的妈妈温柔地问,“我怕飞高了抱不紧,会摔下来,只好放了它。”我面不改色的回答,同时悠然向往地想象被蜻蜓带到高处是何等情景,我那时哪里知道世上根本就没有如此巨大的蜻蜓,最大的蜻蜓早已在恐龙尚未出现的两亿多年前就从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消亡了呢?
我口渴了,东张西望的找水喝。妈妈脸上掠过一抹亮光,一现而逝,又恢复了惯常的平和,可是这表情已被我捕捉到了,我不熟悉,隐约觉得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想趁事情没发生的时候离开,转身刚要走,被妈妈叫住了:“井儿,你过来。”我的头皮紧了一下,一股凉意沿脊梁骨溜到脚后跟。我飞快的回想是否又惹祸了,应该没有呀:衣服没破,只是正常的粘了些泥灰;鞋在脚上,没有被丢在后山;没有招惹对门的丫头,她应该没有告状的理由;今天没与邻村的孩子开仗,既没破皮也没鼓包;家里的碗瓢与书报杂志已经习惯了与它们保持距离,即使有破损,也与己无关呀。在磨蹭着转身的瞬间,我迅速分析了自己的处境,结论是安全。我放心的回到母亲身边。
前面我已提到小妹妹,当时刚出生两三个月,妈妈全部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她身上。所以,我才有了那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支配整整一个下午。在那个漫长的寂静的夏日的午后,我想妈妈多少会感到一些寂寞和无聊,我并不明白身披阳光,满身山野气息的自己的归来,会给母亲带来多大的安慰,我只在后来知道,母亲觉得应该给我一点奖励。
妈妈看了看吃饱后酣睡中的小女儿,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我叫了回来,作过安全性分析的我也乖乖地拢到母亲的身边。妈妈一边拉起衣襟,一面对我说:“嘴张开。”我照办了,并猜到了几分。当时母亲一定处于泌乳旺盛时期,而小妹的食量没有那么大。总而言之,我在断奶4年之后又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到了母亲的乳汁。我眯着两眼,半张开嘴巴,感觉到细细的乳汁在母亲手指的挤压下有力、准确地冲击着我的上颚,间或也有喷溅到牙齿、嘴唇、鼻尖和面颊上。我小小的口腔很快就充满了。我扭过头去,挺直身体,合拢双唇,谨慎地慢慢吞下曾经是我生命之全部的神圣、宝贵的液体。天啊,怎么这么难吃呢?又腥气,又不甜,还粘口!这感觉牢牢地输入到了我的记忆系统并于多年之后的今天鲜明地凸现在我的眼前。
我狼狈地逃回自己住的小屋,继续关注我的俘虏---那些很快就会被我玩死的不幸的蚂蚱---去了。我至今仍不认为那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不过是上帝借我之手稍早一步结束了这些小昆虫的生命。因为这时秋风已经刮起,漫山遍野的蚱蜢们都没几天蹦达的日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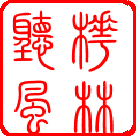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