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
“父亲,您离开我们又已经一个年头了。今天我们兄弟姊妹们带上您喜欢的花篮看您来了,为抚育我们兄妹,您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地操劳了一辈子。现在我们都稍有成就,孙辈们学习进步,母亲身体健康,您老安心休息吧…… ”!站在父亲的墓前,我仿佛又看到了他老人家慈祥的笑脸、我又聆听到了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
父亲1924年出生在郴州安仁县一个有30亩薄田的地主家庭 。虽然只上过一年私塾的祖父生活上省吃俭用、农田里亲躬力做,但他却力排众议,坚持送我的父亲完成了大学学业。这在当时——特别是在我那闭塞、落后的故乡,不能不说是一个觉醒进步的开明举动!
父亲从校门出来后就进入衡阳革命干校学习。衡阳解放的第二天就被分配到解放军衡阳支前司令部负责押送军用物资支援解放广西的工作,广西解放后即调到衡阳百货公司任财会科长。并被选为工会主席、公司学委会主任、中苏友协会会长、市人大代表。1953年衡阳、郴县、零陵三个专署合并为湘南行署,父亲服从组织安排,举家迁移零陵任商业局财会科长,这一年我才四岁。
父亲一生任劳任怨、生活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他和没有工作的母亲要养活我们六姊妹,要供我们穿衣吃饭、要供我们读书学习。因此他自已的两件衣服就得穿几年,仅有的一双皮鞋就必须将就十多年。同事们下班回家休息了,他还须继续为他的子女们劳作。他挑着粪桶,扛着锄头在高山寺开荒地种小麦、种红薯。总得忙碌到点灯了才回家吃饭。那年月,我总觉得父亲不象个干部,倒象个地道的农民。他一身晒得黑黑的、裤脚挽到半小腿。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播种小麦,往每个坑里施底肥,那底肥是用人的粪便跟火灰和细垃圾发酵拌成的。那股恶臭使我们兄弟畏缩着不敢动手,父亲却若无其事地没有丝毫停顿。其实父亲小时候在农村也没有干过农活,我经常想这就是父亲那为人父的高度责任感在鞭策着他吧。记得父亲在晚年时期有一次唏嘘地对我们说,那时候他从没有到好一点的饭店吃餐饭,我心里酸酸的。是啊,那时父母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他们只能辛勤劳作、节衣缩食地计划着过日子。父亲到零陵就享受科级待遇,月工资57.50元,这个标准一直维持到他1980年离休。倒不是政府几十年时间没有调节工资,而是他自已觉得比同事们的工资已经高了许多,每次他都将调级指标让给了同事们,这引起了母亲不少埋怨。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人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认为纯粹是作秀。其实我理解父亲这一行为也是在几十年以后,父亲晚年时已行动迟缓,他当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白发苍苍了)经常来看望他。几十年的旧事重提,大家都深切地留恋、向往当年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的真情实感、那种互不设防的工作、生活环境。我深切地理解了父亲,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确实是不能与当年比啊!
父亲一生从事财务理财和财会教学工作。1953年到1964年地区商业局全权委托父亲在零陵县创办商业财会干校,为全地区商业系统培养财会人员。父亲既当教师又兼校长,备课讲授忙碌不休。日夜都在学校里,连星期天在家里也见不到他一面。十几年时间为全区商业部门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材,可谓“桃李满永州”了。父亲逝世后,老干局派来的一名副局长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肯定了他这段时期的工作:“……如果没有极左路线的干扰,他还能为我们培养出更多的理财能手,他肯定还会有更多更大的贡献……”。我觉得组织上对他的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对父亲多年的付出最大最好的安慰了。
父亲一生平易近人、虚心好学。我记忆犹新的是百货公司一位湘乡籍的张会计,比父亲年龄大了近二十岁,当时已满头银发了,每次来看父亲,总是必恭必敬地叫“老师”。张伯伯很有修养,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古典文学造诣很高。与父亲在一起除了谈他们的本行外,就是切磋宋辞元曲、诗词歌赋之类的著述。父亲晚年时期编著的《人瑞诗词》自述中说,跟张伯伯学到了许多平仄、格律、押韵方面的知识。当然,他们也有意见不一致,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这段忘年交持续了近二十年,直到张伯伯逝世。
“以责人之心责已,以恕已之心恕人”,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要懂得尊重别人,要严 格要求自己。尽管他一生谨小慎微、与世无争,但浩劫和灾难还是没有放过他。文化大革命时期,干校自然是停课了。那时候人们热心政治运动,不再学习业务上的知识了,再则父亲已经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技术权威”在接受批斗。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父亲倒并不感到奇怪,但是,在批判他的人群中,竟然有他干校的学员,这才是使他真正感到痛心疾首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家乡来人要揪父亲回乡批斗。在当时那种不正常的氛围下,卸包袱似的,单位就将父母的户口连人全部都交给他们带回乡下去了。应该感谢家乡大部分淳朴的父老乡亲们,他们明辨是非。在父母最困难、情绪最不稳定的那几年中,给予了他们许多精神上的安慰和实际帮助。但是父母心中的创痛终究不是他们几句质朴的语言能安慰得了的。一个家分成了两个,不在身边的家由几个孩子组成:当时年龄最大的是我姐姐23岁已经结婚,第二就是我,20岁,正在农村插队,还有四个弟妹正在上学。已渐到老年的父母自已每天要参加生产队的体力劳动,学习做农活以获取口粮,最重要的是还得记挂着远在零陵的家、忧虑着需要自已养活自已并且毫无生活经历的六个孩子。这种心灵深处的伤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个时期弟妹们的生活是靠我回城跟当时才16岁就不得不辍学的大弟拉板车、做零工维持的)。值得庆幸的是,捱过灾难深重的几年,我们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解放。1972年,父亲落实政策回来了,户口仍迁回原单位,劫后余生,全家喜极而泣。父亲在他的《人瑞诗词》自述中说:“……在财会岗位上五十年,我讲究的是一个‘廉’字,一个‘勤’字,一生一世将逝,我敢对永州人民说一句问心无愧的话,半个世纪以来,我从末吃过一餐自已不付钱的饭、末收过别人送我一分钱的礼、末要(贪)过一分份外之钱……”。铮铮铁言、掷地有声,我深以为然。古人说:“常在河边站,怎能不湿鞋”,我品格高尚的父亲做到了,他经受住了严峻的审查。母亲更是泣不成声地数落父亲——我倒认为是在赞颂:“如果以前你有一点点过失,经受不住他们四处调查,这次可真回不了城了”。
1980年到1995年是父亲体现自我价值的又一个阶段。父亲在1980年提前办理了离休手续,当年零陵军分区闻讯后即数次登门欲聘他为后勤部财会科长,父亲不听我们的劝阻欣然应聘了。他觉得做这点工作游刃有余、他还能发挥余热。其实我知道父亲心里对极左路线时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多少有些怨气(他提前离休也主要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是想向世人证实自已的才能。父亲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将后勤部的财会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军分区领导称赞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十五年我觉得父亲象干部了,他比年青人还讲究,每天西装革履、容光焕发,我似乎觉察到父亲心中积蓄了几十年的阴霾和怨气消失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当时劝阻他应聘是错误的)。这个阶段父亲的身、心得到了彻底的松驰。正如他自已在《自述》中写的一样:“……心情更加舒畅。在军分区工作这十五年中,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饱览了各地风光……”。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父亲终于调整好心态从艰辛的处境中走了过来。他抚育儿女的任务完成 了,他一生的工作得到了充分肯定。现在他可以、也应该轻松地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生活了。
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全家四世同堂、儿孙绕膝。他常常高兴地筹划年节的菜谱,扳着指头决定设三席呢还是四席的数量。抚今忆昔,父亲总是说体会到了知足常乐的意境。我想世上还有什么比他老人家心情舒畅更重要的呢!
父亲的离去很突然,一点征兆都没有。只是普通感冒,在输完液回家的路上您还说身体没问题,坚持自已走回家。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您怎么就倒下去了?常听老百姓流传说做了好事的人离去时会很快,不会被痛苦折磨。父亲啊!您真的是做了一生的好事?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话您就这样匆忙的走了?
安息吧!父亲!您一生的事业完成得已经很出色了,您的子女们个个遵纪守法,您的孙辈们也大有出息,他们中的佼佼者也跟您当年一样有被选为市人大代表的,您的重孙辈们正在健康成长。对母亲,您在世时已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见过您耐心细致的侍奉祖母。我们会遵循您的教导“爱日以承欢,莫待丁兰刻木祀;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善待母亲,尽到我们的孝道,让母亲的晚年无忧无虑,生活得更幸福。
安息吧!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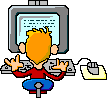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