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上阳峒放歌
按照小何的安排,我们到江永的第一天,在江永县城活动。上午,我们游览了桃川、上甘棠、千家峒,领会着江永三千文化的魅力。吃了午饭后,我们却再也按奈不住急切的心情,决定改变行程,飞车直奔马鹿头工区。沿着当年我们走过的路,进到上阳峒。
1965年9月4日,我们离开长沙。9月13日,来到了江永国营回龙墟农场。9月14日,在马鹿头工区,由长沙市二中(现在的长郡中学)高中87班毕业的十二位同学和初中191、192、197、198班毕业的二十七位同学加上农场派来的五位老职工组成向阳生产队,吹响了向上阳峒荒原进军的集结号。
起初,我们居住在断岭源生产队,每天穿过古木参天的山谷,到山外的山峒艰苦创业。山谷幽深,山路蜿蜒在半山腰,只有正午时分,头顶才透过一线阳光。而今,两边山上的古木差不多砍伐殆尽,阳光直射山谷,在山涧修起一条水泥路,连接起山里和山外的世界。
汽车出了山谷,豁然开朗,拐过山脚,上阳峒的全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上阳峒,这片神奇的土地,背依着山后的水库而旱涝保收,;这是一片刻满我们青春的印记、寄托着我们几多情爱的土地,离开后多少次魂牵梦绕、一旦亲临却又依恋不舍!将近四十年了,我们又回来了!同行的知青唱起了《向阳好》,这是一首当年由我依曲填词的抒情歌曲,歌唱土地、歌唱劳动、歌唱友情,没有受当时世风影响,因而受到队上不少知青的喜爱、抄录在册至今传唱不衰,令我倍感欣慰和骄傲。伴着歌声,四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在创业的最初岁月里,男知青光着膀子挺进深山,披荆斩棘,砍树伐木,女知青头顶烈日,奋战荒原,割伐茅草。肩膀磨肿了,手上打起了血泡,更有那一把把茅草如锯齿,一道道血痕钻心的疼痛,止不住的泪流,但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牙坚持,一天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我们完成了从一个学生向农工的转变。
夜深了,砍茅草的队伍还没有回来,男知青们不顾一天的疲惫,一声吆喝,打起枞膏火,翻山越岭去接人。收工回家,枕边叠好的衣裤散发着清洗后的清香,有的饭量大、家庭又困难的男知青,一翻衣裤:“哟!还有粮票、餐票”,原来是女知青学雷锋、做好事留下的浓浓心意。
一个暴风雨的深夜,一位知青病了,正在痛苦中呻呤,闻信赶来的男知青,忙用木板扎成担架,,抬起病人,冲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过槽谷时,崎岖的山道上,头上是密不见天的参天大树,山道旁是奔涌而下的山水,一失足,将万劫不复。。。。。。。。
终于我们熬过了最初的艰难困苦,在向阳洞的半山腰扎下了我们谋生的营盘、从我们的手中矗立起三栋茅屋, -------三座垦荒者心中的丰碑,象征着团结、友谊和力量。赶在春耕前,我们从断岭源搬入茅屋,我们将“上阳峒”改称为“向阳峒”
今天,我们沿着小路向上,寻找茅草屋,已杳无踪迹,在茅草屋的地盘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男人们都扮禾去了,静谧的村子里只遇见一位老妇人,一打听,才知道,这块地盘仍归回龙圩管理,居民则是夏层铺迁来的移民了。
村落的屋前原是一段空坪,记得当年每天的清晨,我们都列队在茅屋前的草坪,面向东方,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一个豪言、口号风行的年代,我写过一首深深刻着那个年代印记的小诗《请示》,不久发表在省里的一份报刊上,小诗的前四句描摹了知青点的晨景:
上工的钟声飞进早霞,
红色宝书映着朝阳。
我们工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请示心中的红太阳。
小诗的后几段全是震天响的口号,连我也忘记了,但我们在向阳峒的第一年却永远地刻印在我们青春的日记中了。
向阳峒的第一个春天随布谷鸟的叫声来临。我们在荒原上开垦着理想,我们在田野上播种着希望。蒙蒙的细雨中,男知青顶着斗笠,趟着泥水,吆喝着耕牛,在大田里做着阳春;女知青围着青裙,穿行在半山腰的梯田,侍弄着棉苗。一阵歌声,乘着春风的翅膀,从向阳洞美女山的山顶飘落在山冲中水平如镜的田面,驻足向白云缭绕的山顶望去,原来是山坡上放牛的女知青正引吭高歌:
向阳好,
向阳好,
山水秀丽又富饶。
流水欢歌树招手,
高山作屏白云绕。
稻谷香来棉花白,
四季都唱丰收谣。
遍地阳光花儿俏,
都说向阳春来早。
一曲《向阳好》,清亮婉转,激起水中涟漪,也拨动着男女知青的心弦,抹去心中的那一丝丝远离亲人的孤独 和无尽的思念。。。。。。
又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向阳洞迎来了第一个丰收。稻棉田里飞金流银,喜庆锣鼓,敲响在田头。男知青疯狂地踩动着打谷机,就像催动着快骏马;女知青心灵手巧穿行在棉田上下翻飞采摘花絮。晚霞里半山腰食堂的茅屋顶上飘起袅袅炊烟。入夜时分,知青们从各自的茅草屋中拿出小煤油灯。初秋的夜晚,晚会在晒谷坪举行。女知青跳起了从公社知青那里学来的舞蹈《水库上的姑娘》,男知青表演了小组四重唱:《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然,还有《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当月上中天的时分,盈盈月水倾泻在茅草屋、晒谷坪、谷垛、绿树、群山之上。从山中引下的泉水潺潺流过像小鸟扑打着翅膀,,整个世界显得那么清幽、深邃、纯洁。小提琴手扬起了琴弓,秋天的夜空跳动着一串串琶音,接着手风琴以浑厚的和声加入进来,瞬时快乐的情绪感染了每一个人,男女知青不约而同地跳起了集体舞----------尽管在那个年代,跳这种舞已是那么地不合时宜。
我们的生产队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创业的业绩成为农场知青中的新亮点。农场在我们队召开了现场会,不少外队的老知青也来参观,《江永县志》曾这样记载:“囘龙墟农场向阳生产队37名长沙知青,除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外,自建房屋459平方米,开垦水田100亩、旱地70亩,年均产粮1.6万公斤,人均增收69.1元。”
在茅屋里,我们以彻夜的狂欢送走了难忘的一九六六年。新的一年,我们有了新的目标:除保持水稻高产外,还要扩大多种经营,育好柚子苗、试种薄荷、引进果树。我们队派出朱狄去内蒙古学习养牛,准备将蒙古菜牛引进向阳峒饲养,我们还要把茅草屋变成砖瓦房。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岁月奄忽,时移事异。就在我们摩拳擦掌、踌躇满志,打造我们心中的乌托邦和伊甸园时,世态的发展,已非我辈所能预料。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的飓风席卷全国,僻远的山乡也陷入疯狂。四月,农场场部贴出了针对我们队的大字报:“一班由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青组成的向阳队,怎么成了我们学习的典型!?场党委立场何在?”八月,文化革命演变成武斗甚至杀人,一个月黑风高夜,场部考虑到向阳队离场部最僻远安全难以保证,,将我们接出山峒,第二天又派出大卡车绕道广西麦岭,送我们回长沙。一九六八年八月,按照统一部署,我们被分散到工区各生产队,实行最彻底地与当地农民的结合。一九七三年,毛泽东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林信件的批复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开始了知青政策的调整,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我也就是在那年的八月,带着对个人和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沉重思考,告别向阳峒,离开江永的。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经过了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蹉跎岁月的磨练,我们也进入花甲年华。当年那位患急病被连夜送入场部医院的女知青王永汉,现在成了政协委员、知名企业家,她和她先生李静,第一个把可口可乐引进长沙,第一家在黄兴路上开办金店,她被赞誉为拥有国母宋庆龄般风范的女士,受到人们的拥戴。当年那位写下十六字令“干,雄心铸成铁扁担!”并被选送去内蒙古学养菜牛的朱狄,依然像当年那样豪气干天,八十年代他就在长沙五一路上开办了新燕地毯公司,巨大的广告语“祈愿中国和世界都铺上红地毯”一时引起哗动。在茅屋中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学字习画的陈迎楷、汪淮海,分别担任了省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和长沙女画家协会主席。他们画展、书法展开幕的日子也是我们向阳知青聚会的节日。他们取得的成就,是我们向阳队知青的骄傲,而我们队更多的知青则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拓荒牛一样默默地开垦、争得自己一片生存的空间,有人担任了经理、厂长、会计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教师、党务工作者,成为单位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每一位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位成功的知青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但是,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的经历:在人生的花季,我们将血汗、眼泪洒在了 “向阳峒”的每一寸土地。正是在那里,我们经受了艰苦磨练,稚嫩的肩膀才变得坚硬起来;也正是在那里,生命交响曲中奋争的激越旋律成为了最华彩的乐段,引领着我们在人生的长路上不断跋涉。
每年的九月,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往事,还恍如昨日,使人禁不住怦然心动。也许是在现实生活中见得太多的冷漠、浮躁,我们无限珍惜诞生在茅屋中的友情,无限向往知青时代人际关系中的真诚、协作、理想主义与浪漫情调。一位朋友由衷地赞叹道:“在‘向阳’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纯洁、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今天,我们故地重游,心中充满无限感慨。以身后的村落和青山作背景,面对上阳峒的画山绣水,身披夕阳投射来的万丈霞光,我们摄影留念;在我们耕作过的稻田里,打谷机旁,水渠边,在刻下我们的脚印、留下我们故事的每一个地方,都摄下我们的身影;我们甚至不辞辛苦,爬山越岭,走了几里路,到山后的水库寻找我们的记忆:当年暑天收工了,男女知青抖落一肩风尘,跃入山后的水库,让清冽的山水洗去一天的疲惫。我们在水库边留影,聆听风与树林交谈的声音,体味着当年天蓝水碧,青山不老,物我两忘、融入山水的情境。
我们从水库归来,描绘着库区的雅景,嗔怪着谢周迪不去,席地而坐“玩深沉”,真是错失良机,可叹可惜!谢周迪回答说,我不是走不动,只是想难得有机会坐在向阳这方土地上,静静的思考一下,梳理一下思绪。
回长沙不久,谢周迪从电子邮箱中给我邮来一首诗词:
《七律 回向阳》
梦里常忆蹉跎事,竹笠青蓑回向阳。
美女峰下熟稻麦,香花井边洗泥裳。
茅檐情话灯如豆,山径豪歌风亦凉。
卌年重聚时非旧,相携年少谊更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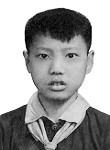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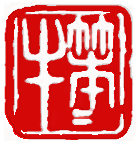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