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永——精神与灵魂的栖息家园(2)
乐 乎
神奇的文字——女书
女书,是记录江永当地土话的一种文字,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男人不识,故称女书。当地妇女通过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在男权思想主宰的世界里,创立了她们自己隐秘的语言空间。
女书的发源地是江永的上江圩镇普美村,这个村子离我插队的公社更近,不到
从县城驱车
村里有个女书博物馆,里面陈列了许多女书书法作品和几十件女书实物收藏品,让我们穿越时空一睹女书的神奇光彩。女书的文字形似汉字但又与汉字不同,其形体倾斜,略呈菱形,笔划纤细飞扬,当地妇女称之为“长脚文”。女书行文自上而下,走文从左到右,通篇没有标点符号和横竖笔划。女书只有1500多个单音文字,但由于它是一种表音文字,一个字可以表达几种截然不同的意思,所以能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
女书是世世代代的劳动妇女用聪明和智慧创造出来的,女书的使用者、欣赏者都是普通女性。女人们用女书编歌和创作,其作品几乎全是诗歌,主要是七言诗,少数为五言诗。女书作品广泛用于女子出嫁,结拜姐妹,祭事和悼念,如《三朝书》、《哭嫁歌》、《四字女经》等,有时也用来纪录历史大事,如《太平天国过永明》、《抽丁怨》等。
女书的传承是母女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数千年男权思想的禁锢,一般女性不能读书认字,妇女于是将自己的痛苦用女书写出来,使被压抑扭曲的心灵得到一丝缓解和释放。女书,实际上成了妇女与命运抗争的武器,成了她们的精神寄托;女书,浸润了女人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在漫长的岁月里,见证了女人的欢乐与悲伤,成为女人生命中最温暖的慰籍。
走出博物馆,漫步来到女书村,路上遇到一位老农,他见我们讲长沙话,也用不咸不淡的长沙话和我们聊起来,我们大为惊奇,问他如何会讲省城的话。老汉说,四十年前,有六个长沙知青在女书村落户,他就跟着学了不少长沙话,如今还没忘,现在那几个知青还经常回来看看哩。
老汉知我也是下放当地的老知青,好象见了亲人一样,非常高兴,热心地领我们在村子里到处转。村里的巷子十分窄逼,两人相遇都得侧身让路。老汉说大家砌房子挨得近是怕老虎吃人,以前这里是有老虎的。村民的屋顶飞檐天窗都紧紧挨着,抬头只见一线天,和广州的“城中村”——员村、杨箕村、石牌村差不多。我说没有自家的禾场晒谷子不方便,老汉说不会,村里有一个公共晒谷坪,大家用簸箕和竹席分开的,从来没有人偷。
老汉自豪地说女书村没有地主、富农,解放时划成分,全是贫下中农。“那文革搞阶级斗争,你们怎么斗?”我好奇地问:“把别村的地主借来斗,做做样子,”我笑了,“借地主来斗”,文革笑话真是无奇不有。老汉说:“我们住在岛上,田地不多,人均不足一亩,所以没有地主富农。男人除了种田以外,还要外出打鱼,靠水吃水,妇女一般不做农活,在家做针线活和家务事。过去生活不是很富,但也不算差。”
我想女书之所以能在这里流传,可能是这里相对与世隔绝,与外界接触不多,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大的政治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四清甚至文革都没有冲击女书岛的风土人情,所以女书能够幸存下来。
踏着青石板路,我们来到女书歌堂旧址。这个女书歌堂也是村子的公房,是村民迎亲贺喜、送葬吊丧的公共场所,平时妇女聚集在这里做女红唱女书,公房自然也成了女书创造和流传的场所。现在这所公房已经破旧不堪,黑黢黢的烟囱不再冒烟。我从窗格望去,里面似有无穷的幽深,门前的台阶杂草丛生,眼前这块曾经产生女书、流传女书的“圣地”,已经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折射出女书生存的无奈处境。
女书发现之初,女书的传人高银仙和她的6个结拜姐妹都还健在。两年前,随着女书的最后一位幸存者、90多岁的阳焕宜的去世,女书许多没有破译的秘密成了未解之谜。现在能够阅读和书写女书的人不多了,好象只有几个人而已。
为了保护这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江永县筹建了女书博物馆、女书文化村和女书学堂,传授学员200多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下放知青也纷纷捐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保护第二故乡的稀世文物。我也毫不犹豫地往捐款箱里塞了几张钞票,以表示对这块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的一点心意。
有报道称,最近几年,前往普美女书村考察调研的教授学者达2万多人次,发表论文150多篇,专著20多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还设立了女书课程。女书这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面临消失的困境,抢救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中华文化的这朵奇葩也需要良好的生存环境,才能长久传承。
但我认为,女书作为一种边缘文化,虽然有着珍贵的独特文化记忆,但她已失去鲜活的生命,我实在看不出需要多达2万多人次的教授学者前往考察调研。中国社会需要研究和探讨的现实问题太多了:三农问题、国企问题、失业下岗问题、教育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等等。教授学者对女书的抢救和研究趋之若骛,有人的确是出自保护中华文化的目的,但也不排除有的人是为了借此出名,或搞一篇论文评职称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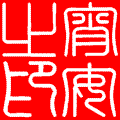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