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下乡之前,需要每个人的志愿书,你要是不写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全校同学的名录贴到了墙上,写了申请的,名字后面是红花,没写的,是白旗。最终,我们统统志愿了。
时间是1968年11月26日,学校的操场一片混乱,开进来十多辆汽车,有客车也有蒙上了篷布的大卡车。满面油汗的军宣队长带领着一些人把下乡同学的名单往车身上贴,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帖到一辆卡车上的时候,感觉很不愿意,要是上到客车上不是更舒服些么?我连忙报告营长,说我们中的几个女孩子晕车,要求换一辆车,他爽快的同意了,把我们的名单换到了一辆客车上,后来我们就随这辆车到了浏阳的达浒。咳咳,虽然这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却也给自己的后来带去了一些变数,不论是好是坏,至少我给自己的命运带去了一点点自主的色彩。所以后来到达公社后要把我们往下分时,我公然混到了决策者中间,在那个明月当空的夜晚,我做到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把几个不相干的同学硬拽到了一个组,其中,我的一个男同学要求我想法把一个女同学安排到与他在一起,还有就是我对我们即将落户的地方进行了简短的调查,知道全公社居然还有一个有电的生产队,于是那个队就成了我们的目标。就在那天夜晚,在公社分配办昏暗的油灯下,我指手画脚的把组成了小组的同学们划拉到了各个大队生产队,小心的把自己那拨人分到了有电的那个队。还有一些同学下来的仓促,我也把他们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做法胡乱组合在了一起,顺便的,把朋友央求的事儿给办了。我第一次尝到了执掌权力的滋味。
回过头来还是动身的那天,株洲的体育广场人山人海,偌大的足球场停满了汽车,车上是即将离家的孩子,车下是送别的亲人。那天我和哥哥随着各自的同学都一同动身,妈妈和妹妹来送我们,再过两个月,我的两个双胞胎妹妹也要随第二批同学下乡了。爸爸没有来,他这时还关在牛棚里,失去自由有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中,我那只有一个独生儿子的爷爷在遥远的乡下故去了,而他唯一的儿子却没能去给他送终,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孤独衰老的奶奶是怎么度过那段凄凉的时光的。广场的四周是五彩的旗帜在飘舞,高音喇叭中奏响着豪壮的语录歌,可是这怎么能掩盖住全场伤心的气氛呢?当汽车发动起来的瞬间,哭声爆发了,那哭声把所有的噪音全盖住了,车上的男孩女孩在哭,车下的父母弟妹在哭,四周看热闹的市民也不由的在哭。老杜当年要不是亲眼见过类似的场景,怎么写得出“....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么逼真句子啊?在一片痛彻心扉的哭喊声中,看着渐渐远去的妈妈和妹妹的越来越模糊的身影,我的鼻子发酸了,要不是看到临座女孩哭肿的双眼就像两颗熟了的李子,觉得既怪异又有些好笑,悲伤的注意力被转移了,我那刚强不羁的形象一定就打了折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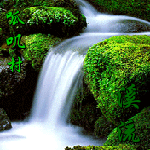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