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在将招工返城的全部手续办妥之后,我背着破旧的铺盖,离开了位于青龙山下的那所小学。在给我送行的学生中,有个扎着小辫子,面容清秀,身材高挑,衣着简朴的小姑娘,她从书包里掏出几个鸡蛋硬往我的背包里塞。望着我渐渐远去的身影,她的眼睛里噙满泪水,直到走出很远很远,我回过头来看,她还站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朝我这边张望……。从此以后,我们便再也没有了联系,她就是我的学生爱云。
我下放的那个山村很穷,在做了六年的农民和农民工之后,迎来了1974年邓小平复出后的治理整顿,其中包括部分地恢复高等教育,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似乎从这件事里看到了一线曙光,便去报名参加了由公社组织的文化摸底考试。没想到,在参加考试的全公社几十名知青中,我居然得了个第一名,但全公社只有一个名额。据说在讨论让谁去的时候,公社党委会上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我成绩最好,不能埋没人才,应该让我去;另一种意见则说我出身不好,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最后两种意见折中:大学不让我上,农民也不让我当了,让我去当民办教师。就这样,我走进了前面说的那所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
平生第一次当老师还真有点紧张,何况我教的还是个一年级新班。全班四十多个学生,都来自附近的几个大队,其中有个叫爱云的小姑娘,个子比其他同学稍高一点,非常羞涩和腼腆,见到生人话都不敢说。我问她多大了?她说九岁。我又问为什么才读一年级?她沉默了。旁边的一个同学替她回答说,她是家里的老大,要带弟弟妹妹,所以爸爸妈妈一直不让她读书。“哦,原来是这样”。按照个头的高矮,我把她放在了最后一排座位上。
也许是好不容易才有了读书的机会,爱云比其他同学更加勤奋,无论骄阳似火还是风霜雨雪,她都从不迟到;每天穿着一件洗得花白打着补丁的花布衣,坐在最后一排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听我讲课,每次作业也都是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成绩在班上居中上水平。我发现她不但学习刻苦,还能做很多的农活和家务事,班里上劳动课,她除了做完自己的那份,还要帮其他的同学完成任务;看到我每天的工作很累生活很清苦,有时放学后她还会帮我洗衣服搞卫生,天气凉了,还会从家里带些木炭来给我烤火,小小年纪,就懂得生活的艰辛,懂得关心和照顾他人。
秋去冬来,一晃两年过去了,我和这些质朴的农家孩子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爱云也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读完了小学二年级,可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了母亲从省城写来的信,告诉我单位即将把我招工返城的消息。这对已经在这个穷山沟里苦苦盼了八年的我来说,当然是个天大的喜讯!于是,我按照母亲单位的要求,很快办妥了相关的手续,想到我的人生又要翻开新的一页,心里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可是,那天当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走进教室,把我即将离开这里的消息告诉我的学生们的时候,没有想到,竟引来了哭声一片,弄得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不管怎样,城还是要回的。临走前,我特意去学校附近的供销社买了些文具,准备送给我这个班的学生们。其中送给爱云的是个浅蓝色的笔记本,当时都兴在笔记本上写几句话,可翻开扉页,我竟不知该写什么好?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在那个年代最流行,也能让她理解的话写在了上面。记得当我把这个笔记本递到她手上时,她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双手在身上擦了又擦,才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我轻声地问她“长大后想做什么?”她想了想说:“像你一样,当老师”,我满意地点了点头。那年她十一岁。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特殊的记忆和我对孩子们的思念,也渐渐地湮没在了繁忙的公务和城市的喧嚣之中。直到今年清明节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才得知当年我的那些学生在我走后,大多都因贫困而辍学了(那时还没有什么“希望工程”),如今他们有的在家务农,有的在外打工,都已经为人父母,有的甚至还做了爷爷奶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爱云,据说也只念到五年级就离开了学校,十八岁那年就嫁给了同村一个比她高两班的男生并有了三个孩子,后来又和丈夫去了离省城不远的Y市,并在那里安下家来,做起了酿酒的营生。
几经周折,我打听到了她的联系方式。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我终于从电话里听到了那个熟悉而遥远的声音。记得当时一拨通电话,我刚开口说话,还没自报家门,她便大声地喊出了我的名字
那个叫三叉堤的小村庄虽然离Y市只有十多公里,却偏僻得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当我们从Y市改乘摩托车到达这里时,爱云和她的丈夫早已等候在路旁,老远就在向我们招手。一下车,夫妇俩便像久违了的亲人一样迎了上来,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彼此的激动。三十三年了,做梦也没想到还能相见!透过模糊的视力,我看到了眼前的爱云,还是那样清秀,还是那么高挑,还是那种腼腆的微笑……,只是三十多年的岁月沧桑,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细细的皱纹。我还注意到,今天她还特意换上了件崭新的衣服,显得十分精神!我突然发现,她身后还有个一岁多的小女孩,正好奇地望着我们。爱云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的小孙女,”然后转过身去喊道:“香香,快叫爷爷奶奶!”我这才意识到:当年那个扎对羊角辫子的小姑娘,如今已经做了奶奶。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仔细地看了爱云夫妇这个简陋的小家,参观了他们的酿酒作坊,还吃了顿乡味十足的午餐。说起当年的那些往事,爱云告诉我,这些年来她也一直在打听我的下落,可是不知道我在哪里?还说在教过她的老师中,我是最让她忘不了的一个!她还说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十多年前,她和丈夫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学会了谷酒的酿造技术。俩口子起早摸黑,小日子倒也还过的去,只是那三个儿子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又没受过什么教育,现在的境况都不怎么好。尤其是老二,两年前在外地打工还患上了重病,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用在了给儿子治病上,仅去年住院就花了几万块……。听到这里,我心里有些发酸!这些年来我的学生一直惦记着我;可我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却什么也没能为他们做。
让我稍感欣慰的是,爱云和她的丈夫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在异乡赢得了一席之地。我们在这里的短短几个小时,就不断地有乡邻来他家打酒,连吃饭时来这里,也是抄起碗就吃,端起杯就喝,就像自家人一样。说到今后,爱云和她的丈夫只有两个小小的心愿:一个是儿子的病能尽快好起来,能自己养活自己;另一个是他们的小酒坊天天都有人来打酒,多挣些钱留给儿子治病和给孙子读书,这就是我的学生——一对农民夫妇的全部希望。
下午四点多,我和妻子又坐上了开往Y市的摩托车,爱云牵着她的小孙女站在路边,望着我们在飞扬的尘土中渐渐远去……。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爱云,今后我还会来看你们的;愿你们的小酒坊越来越红火,愿你二儿子的病能早日康复,愿你儿时的那个梦想,能在你的孙辈们身上实现。
2009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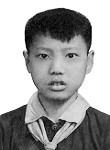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