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家的路是那样漫长,离开第二故乡的女儿这一路竟走了三十五年。
因为听说队上的房子八十年代曾因一场大火全烧光了,生怕自己已认不出村子的摸样,从黎平进入靖县一路向司机打探,直到司机说偏坡到了还反问一句你肯定吗?走下车准确地辨认出村子的方位时心情无比激动,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十四岁的女孩子如今却已是半百老太。
在这里我从14岁长到了18岁。来这里是我人生道路跨向社会的第一步。在梨子树脚虽然只生活了四年,心中的记忆却永生难忘。
还记得初到靖县就去修312公路,妇女队长明月替我担着行李,我只扛把锄头就跟着上路了,紧赶慢赶跟了60多里,到驻地脚底板尽是泡,晚上明月仔细地为我一一挑破、擦干,晚上冷,她把我的双脚紧紧搂在怀里,远离父母的我在异乡感受到了无比温暖的亲情。
与我一般大的桂花、莲英、冬英出工时总是不离左右,教我握锄、砍柴、插秧、割禾,休息时也跟她们学习搓麻缝衲,不过大多数是给她们帮忙。
大一点的务秀已发了人家,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一有空就仔仔细细绣自己的嫁妆。
壬花的母亲多育,20多岁的女儿觉得难堪,晚上常躲在菜园子里悄悄地哭。
酉花幼年丧父,小小年纪就是家里的主心骨,照顾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两个弟弟,锻炼出一副好体魄,干起活来浑身是劲,是远近有名的能干姑娘。
思秀是最漂亮的,柳叶眉、丹凤眼、瓜子脸总是羞答答的,她与同村青年的恋爱为封建家族所不容,最后不得不腆着大肚子被迫另嫁他人,当时看着她哭红了双眼,却没法帮她,深感悲哀。
益泊子(我们队上叫小男孩都是泊子,友泊子、全泊子等等)是我的小兄弟,捆柴的藤条子我总扭不好,他不厌其烦地给我示范,经他指点慢慢也扭得很像样了。
寡妇黄海英大娘是城里嫁过来的,说话柔声细气,走路如风摆柳,因为与家母同姓,对我们时有关照,没事总坐在她家火塘上,看着通红的火苗听她侃古。
螺丝大娘身体不好,行动缓慢,她也时常光顾我们知青居住的凉亭,也不多说什么,一碗马打滚粑粑、一把棕树叶头头做的刷锅刷子都是她的一份无声的爱。
老柏是我们队最棒的男劳力,靖县人盘树过拨是从不多走一步的,可老柏却在过拨时为前面的知青多扛一程。
法老八鹤发红颜,80多岁还爬上大柿子树摘柿子吃,鸭客大爷佝偻着背对一对失去父母的孙子孙女关爱有加,队长婆娘来自贵州,从不出工养得细皮嫩肉,后来才知道她曾是个官太太。枣强妻子二十五、六却满脸沧桑,我差点以为她是娘。
琐琐碎碎的往事在踏入靖县的那一刻全部浮现在眼前,也说不出有多么的重要,也说不出是怎样的心情,可就是历历在目、不诉不休。
只可惜回得太迟,老人们都相继去世,还因为来去匆匆没见到曾朝夕相处众姐妹,听说同龄的冬英去年因癌症去世心里一阵刺痛。
靖县的日子要说苦也是苦,但乡亲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的,我并不觉得那几年自己有什么可觉得委屈,去故地重游也没有什么伤感。倒是乡亲们那份深情令我感动。
“娘哎!你裹老了。”
“你还记得我们啊”
“队上人的名字你怎么都记得哦?”
老柏、明政亲切地跟我聊着往事,明政不断问起他认识的同大队其他知青,如偏坡的李姓兄弟、大吕布、新寨的王兄、王Jl、马家的杨lg等,老柏还说最喜欢听转团湾汤司令(汤哥)讲故事。其实他们心里也时常把知青惦记。
浓浓的乡音、浓浓的亲情,其实我们相互都不会忘记。相处四年其实我们早已是姐妹兄弟,乡亲们比家人更是亲近。
离别三十五年,要说的话太多、太多,当我说下次回来要邀起嫁出去的姑娘们都回村相聚时,乡亲们都激动地说好,大家都盼望着再次相聚。
别了亲人们、别了第二故乡,我还要再来、我们还要再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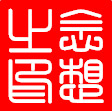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