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丈夫·父亲
我和运兰结婚后,蜜月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缺三少四的日子中度过的。运兰的脸更瘦削了,精神很疲惫,手脚经常用抽搐,看到红薯汤就想吐,总是找酸的辣的吃,她——怀孕了。
作为一个婚后的女人,渴望孩子的兴奋和喜悦,常常会被一种惶恐不安的心情所代替,只感到我们不能再添个小累赘。躲着我曾做过吃不得要吃,挑不起的要挑,跳不下要跳的蠢事。
腹中那条小生命,按照人类繁衍的规律,虽颠虽簸,或坎或坷,仍像坡地上的南瓜,虽没有松土锄草,浇水施肥,也一天天顽强地长大起来。出工的时候,大家恭喜我快要做父亲了,我哼哼哈哈地笑着,想到能和命运相同的运兰扎根农村开花结果,未来的孩子是知青生命的延续,心中的欢悦不言而喻。但是,看到隔壁的玉秀嫂,给两岁多的孩子暖脚,将柴草灰盖在孩子的脚上面,自己外出寻猪草去了,回来时孩子的脚煨熟了。看到那孩子的脚后来成了两根光秃秃的秃柱,于是,对自己未来孩子的命运不免忧从中来。
家里原本养着几只鸡下蛋,“割尾巴”时割掉了。白天出大寨工,田头地角,人们讲吃讲喝,都在美美地回忆曾经享受过的口腹之乐。大家把锄头把子撑在胸前,人一排排树桩般站在那里,嘴巴唾沫横飞,手脚就是不动不做。
到了晚上,我俩坐在火塘边,除了看到千变万化的火苗跳跃之外,再也看不到什么了。我们重复着过去的故事,小声哼着抒情的中外歌曲,运兰说:“火上要是能煮点吃的东西就好了,我好饿好饿。”听着这使我落泪的话,我恨自己不如一只鸡,不能下蛋。我恨自己不如一条牛,不能挤奶。我恨自己不如一只云雀,不能用美妙的歌声,来驱赶她腹内的饥饿和心中的愁烦。
运兰挺着肚子每天照常出工,余暇掰着手指计算,她悄悄告诉我:“预产期到了。”我伸手摸妻的肚子,小家伙在蠕动,仿佛即将破土的春笋,挣扎着要到外面来看蓝天,看白云。我把耳朵贴在妻的肚子上,肚内有咚、咚、咚的响声,仿佛小家伙在说话:“爸爸,妈妈,莫急、莫急,我就来给你们放牛啦!”
吃早饭的时候,我把稠一点的粥碗递给运兰,吃着吃着,她说肚子痛,我以为这就是分娩前的预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慌慌张张提着早已准备好的应用什物,扶着她便往县医院走。
山路崎岖陡峭,曲曲弯弯。运兰总是说肚子痛,负在我背上用手搂着我脖子的力气也没有,我不时将越背越下沉的妻向上耸送,每一耸我就摔下一把汗豆子,运兰就喊一声唉哟。急中往往生智,我蹲下来像马一样,让妻坐在我的双肩上,口里还得、得、得地朝医院飞奔。医生检查后,说是“‘转胎现象”,需住院留观。运兰躺在病床上,紧张地感受着上帝赋于一个女人为了繁衍后代所必需尝受世界最复杂最痛苦的滋味,承担着做一个母亲必须心甘情愿承担的血的代价。
我坐在病床边,抚摸着她的头,给她讲一些快乐的事,逗她开心。我轻轻地在她身上有节奏地拍着,哼着舒伯特的《摇篮曲》。
运兰睡着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忙碌的护士给产房里刚出生的肉团团的婴儿洗抹,打包。偷偷地把手伸到盆子里去感觉水温,向护士和医生问这问那。
我们在医院里,每餐都到食堂买饭买菜,比起在生产队每餐都是吃红薯汤,不知好了多少倍,运兰还吃了一斤鸡蛋,脸色也好看多了。住了五天,总不见运兰腹中有什么动静,医生告诉我,孕妇怀胎足月,过十天半月,甚至月余生孩子的情况都有。为了迎接孩出生,我白天出工晚上摸黑往返几十里山路挑柴卖所攒的钱早已用光,医院拒绝我们再继续住院留观,我又重新做马,让运兰骑着悻悻地回到了生产队。
过了十天,运兰发作了,脸色惨白,冰凉的泪水伴着揪心撕肺般的惨叫顺着面额流淌。羊水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粘乎乎的液体从生命之泉涌出,我吓坏了,赶忙请师傅婆娘月秀姐过来帮忙。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山里女人,简直就是一台生育机器,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年代,她已经创下了生八个儿女,肚内还怀有一个的好成绩。平时我有意问她分娩时的经验,她总是得意地笑着说:“生崽是瓜熟蒂落,三下五除二,自然有个自然,那有什么难的。”
我将剪刀和线放在锅里煮沸,将草纸一张张在火上烘烤,用酒精球在月秀姐和我的手上消毒。运兰折腾了半天后,全身虚弱得像一团棉花。有好长一段时间,她闭着眼睛,咬着嘴唇,头在枕头上不停地左右摇摆,强忍着巨大的痛苦。
对于骨瘦如柴的运兰,子宫似乎毫无张力。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六小时……十多小时过去了,宫口就是张开那么一点点。我已经看到孩子被鲜血染红了毛茸茸的头,如同被卡在夹缝中的一只小兔,动弹不得。猛地踢蹬一下,妈妈就痛得惨叫一声,殷红的鲜血就像小河似地流淌。运兰已经筋疲力尽了。她用梦呓般声音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广生……我不想活了……我想睡……我只想睡啊。”说完闭上眼睛,脸上还露出凄艳的微笑。这是频临死亡的人,被痛苦折磨得冥然不觉,恍然处在一种爱和诗意的意境之中,感觉死亡如同沉沉酣睡和幸福的满足后,在向她的亲人作最后诀别。我感觉运兰已经把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我仿佛看到了地狱中的牛头马面,我的毛发直竖起来。在这关键的关键时刻,如果说运兰睡着了,不如说是失去知觉,在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和任何医疗设备的情况下,大人和孩子随时都会被阎罗王召到地狱去的。在农村,常听人们说起“血糊鬼”的故事,讲得那么荒唐,讲得那么恐怖。这就是说当某女人在分娩时,遇到难产被夺去生命后,就变成传说中四处游荡的冤魂,即“血糊鬼”。运兰,我的爱妻,你可不能做“血糊鬼”啊!信奉唯物的我,不由得第一次双手合十,双膝跪地,嚎哭着虔诚地向主宰万物的上帝祈祷。
我朴在运兰身上歇斯底里地拼命喊道:“千万不能睡!千万不能睡!”我在妻的脸上不停地亲吻,两个人的泪水交汇在一起,就像流过江永的潇水一样。月秀姐急得团团转,也没有办法,只见她面朝东方,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口里喃喃呐呐:“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我把妻的双腿曲起分开,一只手抵着会阴处,一只手拉着她的手,拼命喊道:“一二三用力!一二三用力!”我一边喊一边攥紧她的手。泪水汗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焦灼和期盼的心发出了一种强大的信号启动了妻的潜能,产生了仿佛能使原子裂变的能量,妻在我的号令下,与我密切配合。终于会阴撕裂了,子宫张开了,孩子的头终于向外伸移了一点点,我的孪心几乎从口里冲出来。我重复着刚才的动作,又拼命喊道:“一二三用力!一二三用力!”
上帝被感动了,菩萨显灵了,孩子生下来了。这是一团蜷曲的,颤抖着的,带血的小生命。“哇”的一声啼鸣,报了母子平安,使我和月秀姐心中悬系的磐石落了地。这“哇”的一声啼鸣,顿时给这个空荡荡的知青之家平添了无限生机,一种从未有过我是父亲的快慰和幸福在我的心中油然而起。“是个女娃。”月秀姐抱着女儿喜得流泪大声喊道。我用剪刀给女儿断脐,用线扎好脐带,打来一盆在心中牢记着温度的水给女儿洗抹。我端祥着女儿,大大的眼睛,瘦削的脸庞,两片稍稍隆起的薄嘴唇,是那么像运兰。而那宽广的前额,高的鼻子,圆圆的下巴却又是那么像我。我抱着女儿不停地亲吻,生怕我粗硬的胡子扎了她。我把那粉红色的小手小脚贴在脸上,贴在嘴上我逗她说:“女儿呀!你可认得?我才是你爸爸。你为什么要认我做爸爸呢?你不怕吃红薯汤吗?”女儿看着我笑。我用早就准备好的旧衣裁成的布片给女儿打包,我转过身来抱着女儿给运兰看,她睡着了,真的睡着了,鼻翼一扇一扇的,眼窝还汪着泪水,她实在是太累了。
我把女儿放在她身边,贴在母亲身边的女儿,一会儿也睡着了。我默默地端祥着这苦命的母女俩,她们睡得那么安祥,睡得那么香甜,我却留下了凄楚的眼泪。深感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责任重大。我狠狠地摔掉叼在嘴上的“喇叭筒”,愤然疾起,,从火塘里抓起一根没有燃尽的柴炭头,在门板上写下:“为了让妻儿有饭吃,除了睡觉,我不能休息一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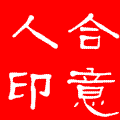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