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在甘棠古坡水库的日子
近两年,常去山水间游历的我,总会多留意在乡间看到的大小水库。农村各地,几十年间耗费不少资源修建的大小水库,不少仍作用于农田水利电力,却也有一些水库仅成为了当地的旅游景点,还有不少小型水库则早已干涸废弃。看到那些大小水库,不论是碧波荡漾的还是干涸废弃的,我总会回想起在下放地曾参与修建过的一座小水库。
我当知青的近五年的时间里,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是呆在了那座小水库工地。几十年过去,不知道曾经的水库是否还存在,它是否仍在起作用?
1972年冬天,我所在的甘棠公社,开始了新修古坡水库的上马动工。于是从各大队生产队为修水库派出的几百上千劳力,扛挑着扁担锄头简单铺盖行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高峰大队的古坡生产队山冲里。我随所下放生产队派出的劳力,也走进了水库工地。
高峰大队所属的各生产队基本都分布在山冲里,而古坡生产队既深入了冲里,又连着了山外。公社驻地甘棠坳,距古坡生产队有十几里地,沿公社粮站旁简易公路下坡,穿过宽敞地域龙凤大队的田垄,进入了乐群大队的鲍家生产队,再绕过乐群大队的大姚生产队,即步入一条蜿蜒山间小路。顺弯弯山路上坡下岭七拐八弯,便走进了山窝里一片稍开阔的地盘,青山绿树的环抱中:几爿田垄,田垄旁分散的三处农舍,一条从山里流出来的清澈溪涧,穿田垄而过,流向山外;溪涧上的小石拱桥延伸了小路,过桥沿小路再翻个山坳,不远即是林木深处中的古坡水库工地。
以后,我知道了那处到水库必经之开阔地,是属古坡生产队地域的——抱树丘,散居的三户农家都姓赵,其中一户赵姓兄弟家的木楼楼上,曾成了我们大队几十名女劳力的大床铺。而我以后又在另一户人口较多的有着双胞胎女儿的赵家,住了很长日子。这期间,还到小拱桥侧边另一赵家,吃过不少餐当中饭的撒了喷香炒黄豆的南瓜油茶,那又粉又甜的老南瓜油茶,至今仍让我回味有余。
过了抱树丘,翻山坳,便见到了夹在山山之间的较大山沟,夹沟延伸至林木深处很远,这夹沟也就是以后的古坡水库蓄水区了。
初到水库工地,所见尽是树木草窠。住处是临时搭建的草棚,多处草棚内已用竹子搭好了一溜溜的通铺架子,铺架上垫些稻草,铺盖卷儿一摊,如同摆咸鱼条儿似地,十几或几十个人一字儿排开,得同挤睡于一个通铺,如此就安顿好了住宿。
劳力队伍大多是年轻人,正当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聚集在了一起,那山窝里可热闹开了。回荡在山窝里的哦呵、说笑打闹、号子声,此起彼伏,难得有消停。那挑土方筑堤坝的活儿,各大队都分有包干任务,哪大队的劳力都不甘落后,都卯足了劲儿比着干,你追我赶。挖土方的,忙着放神仙土;担担子的,单担,叠起的双担、三担,挑着担子快步如飞,挑担队伍有如长龙;筑坝打硪的齐心协力,飞硪起舞,那抑扬顿挫的号子声,震得山响......有月光的夜晚,劳力们通宵达旦,挖土、担担、打硪,比白天还干得欢。记得当时的一句口号是:抢晴天,干阴天,麻麻细雨是好天。
修水库的大队伍中,知青少说也有几十人。记得我所在的龙凤大队派去的男女知青就有十多个,乐群大队也有不少个男知青在工地,认识的寨姓大队知青也来了好几人,其他大队去修水库的知青,我却不熟悉几个。这知青中,有几位还当上了工地的技术施工人员,网友楚牛兄当时就是施工员之一。
工地上的那些活儿,对年轻的我们来讲,算不了什么。伙食中的饭量,我受用足够,只是菜色单一油水少,偶尔有的牙祭肉,是用各色洗脸洗脚盆子装了再分配,不知道吃了几多的邋遢入肚里。住宿洗涮条件却是比较艰苦,十几及几十个人挤在通铺里,那气味那卫生可想而知,久而久之,虱婆子择机而入了。最记得,虽是冬季,大太阳天里,挖土挑担忙得汗水直流的知青们会脱下烂絮棉袄,更卖力地你追我赶。而那些随意扔在坡地上的烂棉袄在太阳底下则亮出了无数光点,那些光点是什么呀,是虱婆子蛋呢!同大队的一女知青将自己的烂棉袄展开,星星点点的成片的虱婆子蛋有好几处,袖腋烂絮处,虱婆子们在争相往四处爬......看得我全身起鸡皮坨,直叫她赶快去用开水烫。
忙碌了一个冬天,古坡水库大坝就在这热火朝天中增高而形成了,水库工程基本完成,劳力大队伍也随之解散。工地上只留下了十几号人手,这留下的人员多为木匠。我记不起自己是如何与寨姓大队女知青LWC,也被留在了水库工地,全公社知青就留下了我俩。以后,我们十几号人的吃住就迁到了水库外抱树丘那户房屋较宽敞的赵家,我和LWC当起了十几号人的管家与大厨,我俩的住处是赵家木楼上的仓房。
水库工地除了我们这十几名劳力,还有县里水利局的负责人与技术人员老罗、老石、正奎等人也常来往于工地。几位干部与我们的关系蛮融洽,任我们如何称呼他们,他们全然没有某些干部的盛气凌人,闲时与我们谈天说地打牌玩笑,俨然是一大家子的亲朋友戚。他们干的是技术指导性活儿,从不为难劳力们。他们与我们吃一样的饭菜,住的也是老乡家,吃住从没有什么特殊讲究。老罗不是靖县本地人,老石是塘头人,正奎姓陈,也是塘头人。
我们住家女主人快嘴快语,是善良能干的乡里主妇。住在她家的那些日子里,在留下的劳力队伍中,是仅有的女性又是知青的我和LWC,得到了赵家妈妈的许多关照。赵家的双胞胎女儿比我们小不了两岁,那俩女孩性格各异,活泼漂亮的妹妹常与我们说笑打闹玩在一起,内向腼腆的姐姐少有掺和,多是静静地陪在一旁,看着我们笑闹。
赵家的偏屋里还住有一对城里下放的石姓母女,石家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不知这娘俩为何被下放。在赵家住了些日子后,混熟了赵家人,与石家母女也混熟了。以后,石家妹子也常和我们闹笑,只是石妈妈却总不敢与我们多言。记得有一天,石家女儿要她妈妈给我看手相,石妈妈却连说不敢为知青看。那年代,谁敢搞那号名堂咯,那可是迷信哦。从没算过命没看过相也总不相信这些的我,生出了好奇,缠着石妈妈非为我看手相不可,还保证不会为难她。石妈妈拗不过我,终于给我看了手相,我不记得石妈妈当时对我说了些其他什么话,不过直到现在,仍还记得她说过的,我以后的婚姻会顺利,儿女会有三四个。那时候,我只听得哈哈喧天,真没将那些话当回事儿。不过,借石妈妈当年的吉言,几十年过去,我现实中的婚姻确实也还好,若不实行计划生育,我也应该会有三四个儿女的吧。
以后我被招工离开了靖县,又好些年后我再调回了靖县,巧的是这返城了的石家母女就住在了我所在单位附近的街道,在城里第一次被石妹子喊我名字时,我还吃惊,靖县城里有哪个认得我咯?
在乡下时,我的胆儿特别小,总有很多莫名的害怕,特别是夜里睡觉常有梦魇现象。我和LWC住赵家仓房里时,有几个晚上入睡后,总觉得有人走进了仓房,走近了床边,我便被吓得大喊大叫,从梦中惊醒好多回。
我以后的住处又搬到了水库坝上的新木楼房里,我又几次在夜间的梦魇中挣扎喊叫,吓了自己,也惊扰了后来的同伴林姑娘与住其他房间的木匠们。隔天他们直问我:小W,你夜里做么个了。我回答:做恶梦哒咧!
水库里蓄水了,水位距坝顶有蛮高,黄浊的浑水没能让我们得利。住坝上的我们,吃水不方便,还是要去坝外低处的水井里挑,挑水的艰苦活儿主要由木匠们轮流承担了。依稀记得,自己也下坝角去担过水。
我在水库工地上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水库干的活儿轻松,工分又不低。继续留下后,我和LWC就是负责十几个人每天的饭菜与核算伙食账。我们的伙食开得简单,除了食盐与部分菜,其他不需要买什么,几个干部该交的粮票与现金都很少。吃的米油,都是各人从家里带来交与的。每餐的菜很少超过两个,基本是一菜一汤,那一汤,是洗锅水里加点海茄子或蒜叶。记忆中,最常吃的菜,是炒海带丝。偶尔也能凭公社供应买回几斤肉,那是少有的牙祭。
我和LWC做事协调得蛮好,两个性子不温不火的人,忙完了活路没有其他去处,就是多与几个姑娘妹子闲玩,还有就是两个人夜晚里数星星。最记得,那夏天的傍晚,我俩常躺在斜坡草地上,任晚风吹拂,尽数天上的星星,数得星星都进云里了,我们才回仓房入睡。
不久,LWC办好了转点手续,她离开了水库,离开了靖县,又远走了他乡。工地负责人心好,想得周到,很快就又安排了大桥大队的林姑娘来了水库,我又有了新伴儿。
林姑娘来了后,做饭的活儿全归了她,我就负责核算与采买。以后的日子,我更清闲了。我闲不住,在工地上撮了石灰,一个人钻到了溪涧里,在涧水不宽不急稍深之处,用石头上堵下截,然后将石灰撒到水涡里,上岸休息一阵,再回到水涡处,总会捡到不少细脬鱼的。那个夏秋天,我就这样消遣了好几回,用收获的细鱼仔改善了大伙儿几顿伙食。
秋天的季节,我还另有收获,清早起来先去捡板栗。我们大队女劳力曾住过的兄弟赵家屋旁,有两颗板栗树,成熟了的板栗常掉树下。我每天早上会先去板栗树下,但不会多捡,只将两个衣口袋装满,这一天的零食就足有了。这样的好日子,令我感觉如同生活在了世外桃源。
后来,上面对我们的伙食费用有了些补给,我去公社买菜的时候多些了。逢赶场日或周末,我会在头一天晚上挑担空箩筐回到生产队住下,第二天买了菜回山里。记忆深刻的一次,又逢赶场了,我又可以回队住一夜。头天傍晚,挽哒裤脚打着赤脚板的我,挑担空箩筐,走在了为进出水库而修能过一辆大拖拉机的简易碎石机耕路上。到农村已有几年,脚底板也早经得磨了,我飞快地将碎石路甩在了身后,到了乐群大姚便走入了田间泥路。
翻过一座小山坳,不远处就是龙凤大队小学校。此时下雨了,雨且越下越大,天也见黑了。小学校是一栋两层楼的烂砖楼,学校里没住人家,附近也没有其它房舍,近处是一片坟地。我平时路过这里总有些害怕,那是决不能去学校里躲雨的。我急中生智,双手提起前面只箩筐往头上一罩,拼命地跑过坟地,任另一只箩筐在身后使劲晃荡。我没有停歇地跑了两里多地,跑回了生产队,雨仍在下。平时胆小的我,那回倒感觉到了自己雨中窘样的搞笑快乐。我常想,那晚那时刻,谁要是正对着我走来,也要路过那坟地,夜雨模糊中,看到那前面一大坨,后面猛晃荡且迅速移动的我,一定会以为碰到了大头鬼,一定会被吓个半死。
窝在水库里自由自在,日子过得惬意的我,与山外知青少了很多接触,熟悉的知青也从没哪个愿跑远路去那山窝里玩。记忆中,我还住在抱树丘赵家时,仅有一次接待过几位进山弄木材的男知青。一天,同大队一男知青带来了几个我不认识的知青,拖了辆板车,说是进山里搞些木材,搞好了后,来我这里吃饭,我满口答应了,然后多准备了些饭菜。搞到了木材的男知青们,来我这里吃了饭歇息了一阵,便推拉着载满木材的板车出了山。
日复一日,临近73年阳历年底,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终于平反复职了,被遣返回了老家乡下几年的父亲,终于回到了长沙原来的单位,我也终于又有长沙的家可回了。不几日,我便告别了水库工地,背上简单行李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住了较长一段日子,直到过完了春节很久,才又回到了生产队。没在生产队呆几天,便又去了大队园艺场。那年年底,我终于被招工,终于告别了近五年的知青生涯。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深深怀念着在古坡水库的那三百多个日夜,怀念那些曾共事的老乡与水利局的几位干部。不知古坡抱树丘那田垄溪涧石拱桥农舍是否美丽依然?那几家赵姓老乡如今生活怎么样?不知古坡水库库区如今的模样如何,它是否总蓄满了一弯清水,它是否在枯水旱季滋润了周边禾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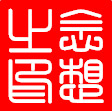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