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哥这名字其实是近两年才叫开的,记得当年在乡下刨食时大家都叫他瓠瓜,这外号出处不详,想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那年月一帮难兄难弟成天琢磨着如何从地里多刨点红薯芋头对付肚皮,哪有闲日子斟字酌句替人起外号?
瓠瓜的爹老子解放前在旧军队里混过事,瓠瓜中学毕业后当然就得下农村改造世界观了。瓠瓜挂着脸盆大的红花下乡时,刚满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满脑瓜 子乌托邦似的理想,每当他扶犁掌耙吆喝队里那条大水牯时,岭前坳背便拖一串铿锵的回音。农事的间隙,瓠瓜最喜欢摆弄他那架破收音机,每次去允山闹子赶集,别人忙着称盐打油,瓠瓜却跑到公社农机站“研究”那台老掉牙的拖拉机去了
那年6月间,全队人在打鼓坪扮禾闹腾得正欢时,有台打稻机忽然不转了,光头队长急得跳起脚骂娘,只见瓠瓜不声不响走拢去,蹲下身子鼓捣了才一盏茶功夫,那机子就轰隆隆响起来了;公社召开农业跨纲要动员大会那次,革委会主任在台子上正讲得吐沫横飞,喇叭匣子冷丁哑了,瓠瓜当时勾着头躲在人丛里打瞌睡,有人好不容易找到他,他于是揉揉眼睛,趿一双烂拖鞋不急不缓走上台,围着那几个铁匣子这里摸摸,那里碰碰,真神!主任那抑扬顿挫的声音立马又萦回于公社社员的耳际了。
瓠瓜年长我们几岁,自然比我们“懂事’”得早些,下乡两年后有人便发现他与队上一名女知青有点“那个”,那位女知青人长得体面不说,持家理事还十分能干,尤为令人称羡的是,其家庭出身乃毫不含糊的工人阶级。这“红与黑”二人你来我往、两情相悦,不久便结为连理,共一口鼎锅煮饭吃了。队里有人阶级觉悟高,知道瓠瓜是另类子弟,评工分时常与他过不去,瓠嫂虽系女流,却不信邪,每遇事不公允,必锣响鼓响与人理论,队里人惧于瓠嫂天牌硬扎,只得网开一面,瓠瓜倒也为此省却了许多烦恼。
瓠瓜率一家五口回城那年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喧嚣的都会对他早已失去了诱惑力,何况瓠瓜在城里连个窝都没有,又何况在城里做普工一个月才32元5角钱,可一家五口嘴巴接起来尺把长,拿什么来糊口度日?因此回不回城并不十分在意。不料他泰山大人高瞻远瞩,接连几通来示,硬是将他召了回来。一家五口便揳住在岳家那本就狭窄的的过渡房里,白天人多打不得转身,晚上便把门板卸下来打地铺。瓠瓜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得委身于一家羽绒厂做临时工,牛高马大的大老爷们,天天坐在矮板凳上与婆婆老老一起选鸭毛。
幸亏瓠瓜在农村时学了几手养身的手艺,后来他应聘到一家街道小厂做电工去了,电工之外,车钳工刨铣诸工种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不久就被举荐为这家厂子的厂长。
要说瓠瓜,还真有点能耐,街道厂子干了一家又一家,任凭潮起潮落,这些厂子不但脚跟站稳了,并且产值连年递增,职工效益亦稳步上升,两个儿子自小就跟着他在厂子里混,衣钵承传,长劲特快,驾驶、电工等执照尽入囊中,谋生技艺于他父子而言,自是小菜一碟。
瓠瓜小有名气了,他早已获得工程师职称,并被转为国家干部,级别虽不高,好歹也是政府官员了,听说他后来还连任几届区政协委员,与上级首长平起平坐、共商国是呢。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这帮刨泥巴出来的老知青有的退休,有的下岗,大家相聚的机会又多了起来。瓠瓜不知何时已经赋闲,如今入则含饴弄孙,出则提篮小买,日子倒也过得安逸。
每遇友人招饮,我常忝陪末座,瓠瓜自是座中常客,有一回酒酣耳热之际,只见他膝头上的小外孙忽然惊呼:外公有白头发了!闻之满座讶然:是啊,瓠瓜早已为人之祖,再要这么叫法,实在不恭,于是立即拨乱反正,一改“瓠瓜”为“富哥”,这一过渡,自然无痕,不知富哥有所察觉否?(原载《空中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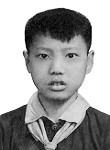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