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乡插队杂忆(10)
煤 油 灯
乐 乎
天黑了,我在茅屋里点燃一盏煤油灯,漆黑一团的屋子顿时光亮起来。煤油灯的火苗是那么微弱,风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火苗被吹得左右摇晃,黑烟升腾缭绕,但足以看清牛粪泥巴糊的芦苇把子墙壁了。小心翼翼地用手掌围住火苗,将煤油灯放到堂屋里的灶上,点燃柴草,开始“烹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晚间大餐”……
下放江永时,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手电筒,还配了几节电池,说山区没电,还有野兽毒蛇猛犬,晚上外出带着,以防意外。母亲的关怀温暖着少年的心,夜晚走路、上厕所都带着手电筒,好象母亲就在身边,它仿佛就是我的保镖,使我心安且无所畏惧。然而母亲考虑不周的是,带去的电池用完了,哪里还有钱购买新电池,手电筒没了电池,就犹如枪支没有子弹,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还是煤油灯好,实用而且费用低,在乡下,昏暗的煤油灯伴随我度过了艰难日子,她那那微弱、幽暗、颤动的光芒,在心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以至我在办公室和家里书房还刻意摆放着几盏简陋的煤油灯,每当抬头看见它们时,便回忆起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煤油灯成了激励我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指路明灯。
最简单最原始的灯只需一只瓷盘,浅浅地盛上一层菜油,加上灯芯草或棉纱线,点燃就成了一盏灯。人们为了省油,平时只点一根灯芯,火苗似黄豆大小,照亮身前身后的一小块地方,若来了客或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才会同时点几根灯芯。
刚下农村时还见过这种瓷盘灯,但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普遍用上了煤油灯。煤油灯的制作工艺简单:先在小玻璃瓶(多半是墨水瓶或药瓶)的盖子上钻一个小洞,插入一根薄铁皮或铝皮卷成的细管,管内穿一条棉纱线作为灯芯,瓶内灌上煤油,一盏煤油灯就大功告成了。这种自制的煤油灯没有灯罩,燃起来屋里便充盈着煤油味,一颗黄豆大的火苗东倒西歪,要是有人走动,人影便会晃动起来,活象皮影戏中手舞足蹈的妖怪。
再后来,供销社有带灯罩的煤油灯买了,这种煤油灯上了一个档次,由玻璃灯座和玻璃灯罩两部分组成。灯座灌油,盖子连着灯头,灯头上有一根带齿轮的横轴,可调节灯芯,灯罩插在灯头上,靠突出来的几片小铁皮夹住。灯罩上口小下口大,中间成弧形。这种灯的设计比较先进,点燃后明亮又不冒烟,没通电的地方至今仍在用。
但煤油灯罩的内壁很容易熏黑,必须经常擦拭,否则会影响亮度。先向灯罩内“哈”几口气,让灯罩沾上雾气,然后用一块旧布伸进去轻轻地擦,用力过大,玻璃会破裂,我就擦破过几只灯罩。另外,每隔几天就要调节一下灯芯,将枯焦的一截剪去,美其名曰“剪灯花”,以保持煤油灯的亮度。
煤油是凭票供应的,数量不多,却很少人说煤油不够用。为节省煤油,人们要等到天几乎完全黑下来才点灯,而且早早就上床睡觉了,在黑暗里,许多超生的小孩就是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生了出来,这也难怪,农民在漆黑的夜里能干什么呢。
很少听农民说煤油不够用,但火柴不够用的抱怨却经常听到。火柴也是凭票供应的,如果家里有人抽烟的话,那火柴的确会发生危机,“借火”、“借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来引进了打火机,大受乡亲欢迎,打火石也是凭票供应的“控购物品”,非常紧俏,知青回城探亲总要想方设法带些回来送人,便于携带而且极受老乡欢迎,很长一段时间,打火石成为仅次于长统套鞋的馈赠礼品(主要用来“拉拢贿赂”手握知青命运大权的干部)。
几年过去了,生产队只剩下我一个知青,夜幕降临时,我常常对着火苗摇曳的煤油灯发呆,被彷徨失落的灰暗情绪笼罩着,觉得前途渺茫,农村生活可以磨练我的筋骨,强壮我的四肢,却无法驱散我的颓废、迷惘和孤独。独自面对那盏煤油灯时,眼前浮现的画面伤感而暗淡,凝视着煤油灯飘忽的火苗,联想自己的处境,虽不甘命运的摆布却又无可奈何,不知人生归宿在何方……
“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曾是农民兄弟几代人的追求,这一追求现已基本实现,煤油灯早已被淘汰,吊灯、壁灯、台灯、射灯各式灯具都进入了乡间农舍,照亮了农民兄弟的居室,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盏陪伴我度过许多雨雾弥漫夜晚的煤油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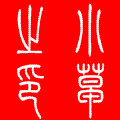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