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婚那一天
应邀参加晚辈们的结婚典礼,款步走进豪华气派的宴会厅,喝完喜酒后,坐在布置得五光十色的新房里,给新人说些祝福的话,听着旋律优美的乐曲,我常常会想起自己结婚的那一天。
四十年前,是我们插队落户第五年,队上原来有五位知青。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齐心想办法,还能弄点东西塞进肚子。以后,投亲靠友和转点先后走了三位,村子里就剩下我和运兰了。相依着同吃一锅饭(粥、红薯汤和野菜等),同点一灯油,同说长沙话,同唱知青歌。
就在这个时候,运兰父母揣着运兰的放大相片,拜托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给女儿牵线搭桥。于是,工厂的工人,军营的军官,铁路上的火车司机,都被相片上运兰那清纯漂亮的容貌、响当当的工人家庭出身所倾倒,寄来很多承诺能从糠箩跳到米箩的求婚信。
运兰看完信后,不以为然地递给我,我坐在火塘边,一方面为她有一条活路而高兴;另一方面想到生活中的唯一知己,日夜渴望能成为自己妻子的人,即刻就要变成一只小鸟远走高飞,想到她走后我的孤独,我的痛苦,我的悲伤,再也不能阻挡的泪水像溃堤似地刷、刷、刷地从脸上流下来。
运兰递一块毛巾给我,笑着说:“哈宝,五年了,你还看不出?我的心属于谁?你就像梁山伯,只会痴,只会哭,你就没有勇气开口说一句话?”顿时,一股爱的暖流涌遍我的心身。每二天,我俩手牵着手,一路歌声一路笑,翻山越岭到公社去登记结婚。
用我的师傅生产队长小保的话说,广生和运兰的姻缘结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做的媒人,我们贫下中农要把他们的喜事办得热闹些。
队委会决定:全队放两天假。一天让社员挑柴到县里卖了有钱送礼;一天婚宴中所涉及的大小事务,全部落实到人,由队上统一记工分。队上开仓称了两百斤谷,体面地让赴宴的宾客们吃一顿不杂以红薯丝的饭。我和师傅小保挑着箩筐木桶到县肉食站,凭结婚证和县知青办的介绍信,苦苦恳求卖肉的领导支持知青生根开花结果,买了十二个猪头,十二副肺叶,四十八只猪脚及猪血肠子等下水。
小保师傅早就四处吹风:喝喜酒者,送礼一元。大队所辖的五个生产队的田头地角,把我们结婚当成新闻讲得沸沸扬扬。人人脸上都喜笑颜开。劳力都到县城卖柴去了。不能卖柴的也想方设法准备红蛋四个或挂面两斤,相约都来喝我们的喜酒。
结婚这一天,按当地风俗:新郎新娘的头发要用茶油梳得溜光,脸上要用红纸浸水涂抹得通红。我苦苦哀求做伴娘的“铁姑娘”们,并偷偷塞给她们每人四颗糖,她们才同意免去这些花里胡哨。我从山上采来映山红和各色野花,做成一个花环,深情地戴在运兰的脖子上,这便是我送给新娘最厚重的结婚项链。运半穿一件蓝色打了三个补钉的春秋衫,满脸泛起红晕,更显得娇柔妩媚,楚楚动人。在我心中,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我牵着她的手到每家每户,给为了我们婚姻大事操劳的伯爷伯娘,叔叔婶婶鞠躬致谢,接受淳朴的山里人给予我们良好的祝福。渐近良辰,社员和知青好友蜂拥而至。其中不少人是“阿凡提”故事中“朋友的朋友”,师傅小保虽主持过几回这种事,也急得抓耳挠腮,来来回回地走,来来回回地吆喝。我只好耳语他将所有的菜都来个“兔子汤的汤”。司宴官看着竖在禾堂标杆的日影,大声宣布良辰到——顿时鼓乐齐鸣,人群中欢声雷动。我们没有按照江永那种跪跪拜拜古老的结婚程序,在证婚人小保师傅的主持下,我和运兰虔诚地给大媒人毛主席像三鞠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然后,依次给贫下中农三鞠躬,给师傅师娘三鞠躬,给远在长沙的父母三鞠躬,最后是夫妻对拜。完了,当众亲嘴一个:学着猪八戒的样子背着运兰在人群中绕一圈后再背入洞房。
队上的社员都如同是自己家里嫁女收媳妇,搬出所有的锅盆碗筷,桌椅板凳,仍不能解决赴宴人数“炸箍”之急。我以新郎的名义当众宣布:女宾先吃。这不谛于平地一声雷,惊得小保和男人们瞠目结舌,几乎不敢相信我的决定是真的。
江永传统习俗:别说喜庆婚宴,就是家中平常来了普通的客人,哪怕是喝红薯汤,妇女也只能站在桌旁伺候,是不能上桌同吃的。只有知青才斗胆向横霸一方的传统习惯势力挑战,而且时间就在自己大喜的日子里。老少爷们仰脖长叹,只能是耐心地等待着。令饱受欺凌虐待的山里妇女们欢呼雀跃,平生第一次坐在知青结婚的正席上喝酒吃饭。人人个个得意地看着平时对自己骂骂咧咧挥拳跺脚、现在站在桌子旁边吞口水的窝囊男人。一个个脸上绽放着翻身得解放的欢笑。待女宾酒足饭饱,男宾上桌,已是午后。其中不乏“合二为一”者,没吃早餐,腹内空仓。山里人都有豪饮的性格,特别是喜酒,上桌必来个“四喜财(四杯)六六顺(六杯)”,几杯烈酒下肚,早已倒翻数人。有的连先天晚上所食都呕了出来,似乎酒中都掺有蒙汗药,面对着久违了的猪头猪脚及其它好菜,也只能干瞪着眼睛。众人谅我先天惧酒,闻酒便醉。却都知道我是一个三条泥鳅一瓢水,五个辣椒水一瓢的“汤将军”。司宴官约法三章:令我手端大碗萝卜汤,以汤代酒,携妻依席向众人敬酒,客人饮酒一杯,我便喝汤一碗`。一席十人我便喝汤十碗。席中妙趣横生,笑声在峰峦沟壑中回旋飘荡。每敬完一席,我必跑入茅屋尿尿一泡。大娘大婶,给我们送来枣子花生,祝我们早生贵子,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知青好友,有的将自用的脸盆、床单、肥皂、热水瓶等赠于我们,说:凑合像个家。有的苦于囊内空空,便顺手牵来一只鸡、一只鸭。更有甚者,牵来一件衣,牵来一条裤作为馈赠我们的结婚礼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只有非常不幸的人才有怜悯别人的权利”。在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日子里,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下中农、知青战友们,统给予了我们人世间最诚挚的爱。我和妻把这种人间仅此的真情珍藏心中,感谢动得让无限委屈无处伸诉的泪水,像山里的溪流,汩汩地在面额上流淌。我们与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与知青兄弟姐妹永世难解的缘分情结,无法能用语言讲清楚道明白。深夜,宾客散尽,我们步入洞房,将两张床拼成一张床,将两床被子垫一床盖一床。我们用诚实的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我举起右手,向妻起誓:“今后一定尽到丈夫的责任,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竭尽全力让你生活得好一点。”洞房内,依然如旧,只有那盏煤油灯在闪烁,像上帝的眼睛,在窥视着当代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在新婚之夜,忘却了一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的相册-
我的相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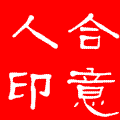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