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早以前就听说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梵语。梵文是古印度语言,我连古汉语都没有过关,研究古印度的季羡林的著作肯定读不懂。
《人物》杂志从1991年第4期起连载季羡林《留德十年》。刚读第一篇,季羡林那极具亲和力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双月出刊的《人物》杂志,让我时时盼望出新刊,长达一年的时间,分6期才连载完。读完《留德十年》,我知道研究古印度文字的教授,写出的文章清新流畅,平易近人,读他的文章如同听一位北方老大爷讲过去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季羡林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家乡济南谋得一中学教员的职务,教了一年国文后,他考取了清华赴德国交流的研究生。去国离乡,赴西方留学是当年青年学子最时髦的事,季羡林春风得意。原以为两年后可以回国,不料二战暴发,交通断绝,回国无望,季羡林在德国待了十年。他先后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获得博士学位。
他初到德国时,先在柏林做暂短的停留,转赴哥廷根,他租住在一对中年夫妇的房子,在这座德国小城一住就是十年,与房东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就读的哥廷根大学有很浓的学术气氛,数学家高斯曾经是这所大学的教授,物理学家韦伯在这里发明了电报。他学的梵文专业只有他一个学生,老师也不介意,照常上课,一丝不苟。二战后期,盟军飞机天天轰炸德国。哥廷根很座只有2万人口的小城,也遭遇过几次轰炸。有次盟军飞机在哥廷根投了2枚气爆弹。季羡林见到流体力学专家、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普兰特尔教授在一段短墙下弓着腰,原来他是在观察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段短墙的,教授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在慕尼黑,一天夜里,盟军飞机正进行地毯式轰炸,人们纷纷跑向地下室躲避。而一位老头反其道而行之,从楼下冲向楼顶,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作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美军进攻哥廷哥时,少量的德军做了轻微的抵抗,美军一发炮弹落在季羡林的老师西克教授住房旁边。战火刚一停止,季羡林赶到西克教授家,他正在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碎片洒落在书桌上。
德国学者就是这样,宁愿为科学而舍命。
战争结束了,季羡林没有选择留下,而是急于寻找回国的途径。经瑞士,辗转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他在英国时拜见了陈寅格先生,陈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聘季羡林为教授。他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从那以后,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做了几十年的教授。
我是从《留德十年》“结识”了季羡林先生,后来,中国出版业印行了大量季羡林的书,我的书架上有《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读书治学》《牛棚杂忆》《季羡林散文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没有一册季羡林的学术著作。
有年秋季北京大学新生入校时,季羡林独自站在校门口,看着成群的新生步入校门。忽然一位女生向他求助:她要去办入校手续,请老师帮她照看三件行李。季羡林欣然答应,一直等到那位女生办好手续,回来取走行李。新入校的女生没想到,那天帮她照看行李的是北京大学老教授。
读季羡林的《记张岱年先生》:“我有一个自己的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知识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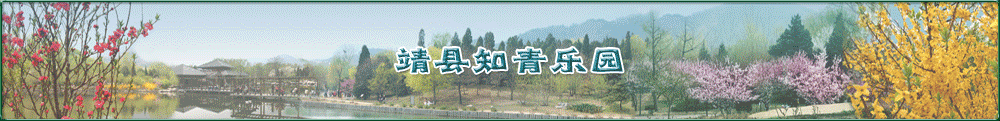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