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娭毑肖瑞云
我的娭毑肖瑞云。她老人家于1902年12月21日生于株洲盘石。
盘石肖家一族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开创了湖南早期工业—-长沙猴子石玻璃厂,她少年时曾在这里作过描花工。娘家不富,有姊弟7人,她排行第三,两个老弟都是吹玻璃的行家老手,老满冬姨娭毑为人极善,早年在长沙缝纫学校学习,追求进步,参加共产党,与杨弟甫、陈素、陈明、刘乐扬、易秀娟一块搞地下工作,后来跟学识很高的丈夫搬迁去北京。那时娭毑对姨娭毑参加革命不甚理解,但有一次姨娭毑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带着易姨逃到三门我娭毑家,我娭毑娭没说二话,把她们藏在阁楼上,送饭给她们吃,使她们躲过这一劫。毑的侄子都长得“体面”、聪明,肖希平、肖希正兄弟是这样,解放后长沙热水瓶厂高级工程师肖彦云也是这样,令老人悬挂在心的是:年仅14岁的肖伯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去向不明。
娭毑18岁嫁到三门李家,丈夫李振球,在设于长沙的湖南公立法政专科学校毕业,长年在外谋职,1943年因胃潰疡病逝于衡阳仁济医院。她41岁守寡。因家产一直由公婆掌管,很受公婆管束,加之日寇侵犯,土匪抢劫(1948年土匪夜袭,胁迫老祖母将家有黄金悉数掠走),使她对封建礼教、男女不平等、社会动乱不满,对新社会抱欢迎态度。我们三兄弟都是她老人家一手带大的,虽然她没有读过书,斗大字不识一个,但却是她老人家对我们兄弟的影响,为我们日后的自强自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娭毑勤劳主持家务,我父母亲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忙于公务。
娭毑的外表是老土老土的,常年穿着一身黑色粗布父母装,衣襟上插着一条干干净净的手帕,剪着齐耳短发的头上系着一块泥巴色方头巾;她一双粗得像松树皮一般的手做起事来很麻利,一双裹过后松绑的半大小脚走起路来一阵风;她老人家那一双常年被沙眼“倒扎毛”引起泪水的眼睛,闪现着和善慈祥的亮光;那一张被微皱的腮帮夹着的紧缩着的尖嘴巴,显示出她刚强泼辣的性格特质;那一副抿嘴笑的开朗的神态,洋溢着她满足于生活现状的喜悦之情。娭毑不怕苦,不信邪,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对媳妇看得重,对子孙更是慈爱有加。记得儿时每当闷热难当的夏夜,我总爱睡在被她抹得“秋凉秋凉”的竹板上,一边听她讲岳麓山蟒蛇洞一类的民间故事,一边享受着她为我打扇、摸背的舒服,渐渐入睡。1958年,我家由药王街保险公司宿舍搬至尚德街银行宿舍,娭毑除了承担家务,她还当过尚德街民办公共食堂的炊事员,当过市清卫处每月18元工资的街巷清扫员,并且担任了宿舍的家属委员。她什么都乐意干,打扫宿舍卫生,讲公道话,甚至连邻家的一位媳妇临产,不喊自己的婆婆送医院,却喊我娭毑帮忙。可是就是这样好的老人,为了使我们少挨饿,到马路边摆了几次地摊子,卖我爹从株洲批发来的几片铜调羹,竟有人向领导举报她“投机倒把”。
1965年四清运动,父母亲被迫送“地主”母亲回老家。尽管在我们宿舍这并不是稀奇事,还有洪娭毑、肖家外婆、罗妈妈等老人均在此列。但是我娭毑生性好高好强,她是在我们弟兄三人还处于睡梦之中,悄悄走的。
在三门镇的12年时间里,尽管受到当时阶级路线的严厉管制,但是她帮人带小孩,搓麻,纺纱,在自家门前种几兜烟叶,闲时独自坐在家门口吧几口水烟,挺悠闲自在。对于“劳动改造”,她从不含糊,有一段时间里安排她扫街,她老人家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穿上黑褂子,戴上泥巴色头巾,提着自己买的扫把,跛着小脚走到街上趁黑扫起来。信迷信但又胆大的老娭毑扫到闸口时,常常遇着过路人歇脚放在堤边的死尸,娭毑这时一边扫,一边嘴里念着:“好人啊,我不是赶你,我是在为前世赎过!”娭毑以此壮胆。娭毑的每次卫生清扫都是在天亮之前结束。
文化革命的劫难中,尽管她被屡次戴高帽子游街,她倔强地说“这有什么丑的,我又没有偷人养汉!”。甚至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吊她“半边猪”来逼供讯,但她临危不惧,厉声斥责那个坏家伙:“我只不过是犯了人民政府的土地法,你呢?哪个不晓得!你过去就是尽作恶的圈子里的土匪,”。
尽管娭毑“天不怕,地不怕”,她还是有一怕,就是只怕运动秧及子孙。自从1965年我爹送“地主”母亲回老家之后,母子俩一直没有相见,甚至有一次“五类份子”(戴地、富、反、坏、右政治帽子的人)在株洲市体育场集合受训,体育场离中心区人委近在咫尺,她都没敢去看儿子。直到1976年,娭毑被摘掉地主份子帽子回到长沙之后,母子俩才得以见面。
我们下农村时,娭毑独自住在三门镇,很是念叨我们,有一次她竟捎给我们1丈多用她亲手纺的纱所织成的布,尽管这种大布做的衬衣很粗糙,可是我们穿在身上却暖在心头。我们也趁回长沙到株洲的机会,去三门看她老人家,去了就帮她买煤挑水。1975年寒假我去三门带去了一大捆在我任教的小学里种的烟叶,我的烟叶收得嫩,怕不合娭毑的意。但她老人家接到后,很珍惜!还总是在说我的好。以后,我脑海中浮现出娭毑老人家用“纸迷子”点燃塞在那杆擦得铮亮的铜烟袋口上的细烟叶,然后瘪着尖嘴巴吧嗒吧嗒吸烟的神情 ,那是一副怡然自在的神情。
娭毑住在老家从来不搭信要钱要物,倒是乡下的一些亲戚喜欢找我们帮忙。记得1970年姨公公写信给我,说要嫁女备嫁妆,托我买10斤皮棉弹棉絮。我下放的垸子是产棉区,皮棉容易买到且便宜,但路途遥远不好送。为了送那一大麻布袋棉花,我不得不专程从岳阳搭火车直接到三门车站下。记得下车时已是夜晚,四下黑漆漆的,寒风刺骨,当我背着这“庞然大物”,好不容易摸到刘姨公家屋基前的田垅,不意失足跌落到水凼中,弄个混身透湿。住在三门街上的娭毑知道了此事,她非常心痛,不由分说,把随后过河来看望的刘姨公骂了一顿。刘姨公不但不恼,反还夸道:“你崽的个性像你,你孙子的个性也像你啊!”
那次,我从三门回到爹爹身边,我伤心地告诉他,“寄给娭毑的15元生活费,要付房租,买煤米油盐,实在不够!”说着我不自禁地掉下泪水,铁石心肠的爹也黯然伤神地答复我,说:“钱寄多了影响不好,有人去三门,我会多搭点去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路线以后,中国大地解冻了,知识份子获暖还春了,我们家庭也从长期分离的困苦之中解放出来。记得1982年春节,我和梅睿完婚不几日,爹爹从株洲回来了,妈妈换任刚恢复的保险业务,大弟夫妇带来了1980年10月出生的正在牙牙学语的孩子(现在已是中信集团的项目经理),小建带着女朋友从岳阳同来长沙。那天家庭气氛特别热烈,我用学英语的盒式录音机录下了大家的即兴讲话。弥足珍贵的是娭毑的声音—-我们后人耳熟的湘潭方音,她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说:“祝愿你们新婚夫妇粗话细讲,和和气气,白头偕老!新媳妇要堂前教子,枕边教夫;如今新世界好,过去电视机看都冒看过,电褥子听都冒听讲过;你们年轻人拿起多做不要紧,老哒享福,我现在不就享福哒!”娭毑的话语亲切、质朴、风趣,令我们这些受时下“大话”、“套话”影响的后代自叹不如。
娭毑于1985年12月16日在长沙市小吴门局后街银行宿舍安然辞世,享年83岁。去世前她老人家头脑仍很清醒,嘱咐我,“枕头下5块钱莫丢了!”尽管她生前患过胃病,急性胆道炎,但她从不愿看病吃药,不愿多花费,以免增加后人的负担,而她每每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疾病的折磨。娭毑是老死的,娭毑是娭毑这代人中寿命最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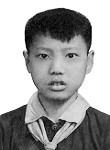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