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姐妹情
(之四)
就这样我们又重归于好
牛背上的惊险,将吆吧无情的抛在了堰塘中并在众人面前出了洋象,可想而知,吆吧与三个放牛娃的关系也因此一落千丈。
哎!恨只恨那头愚蠢的大公牛干嘛不长脑子,在田里跑踩坏秧苗也罢了,却要跑到堰里与吆吧共“舞”?更气愤的是这个畜牲跳进水中后竟将吆吧甩到一边,自己露出半个头在那里哞!哞!哞!的直叫唤,似乎向众人宣告“我大牛胜利了”。
这件事的发生,无论怎样解释,三个放牛娃始终逃脱不了干系,为了弥补过错,我们也总是千方百计的喊着吆吧、讨好吆吧、巴结吆吧,但吆吧再也不与我们搭讪,要不就是辟天盖地的一阵臭骂,骂后再说:“我才不想张你们,气死我也”!说完甩开两个手膀扬长而去......
“双抢”结束后,趁着下雨知青们都未出工,惟有三个放牛娃去山边放牛,放牛的山树木茂盛,别人看不见我们,而我们却一眼就能望见来自三个方向三条细若游蛇的小路,只要那条小路上冒出了人影便会互相猜着,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或少的?待行人走近是认识的便侃会大山,少不了寒喧一阵,不认识的也要评头论足来一番讨论,就这样没话找话,没事找事的打发时间。
这时,只见小路上又有了行人,我们便放弃讨论又开始寻找新的话题。只见来人手舞足蹈、走路象跳舞,停停、走走不知在忙啥?待看清来人时我们三人都惊叫起来;“哎呀!那么是吆吧啊(因为知青队从没有一个人外出的习惯),她这是到那里去呢?”带着一头雾水,我们三人目不转睛地死盯着吆吧不放,生怕她从我们的视线中溜走消失,直到她走到了一栋土屋前,跨进门没了身影,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开始了跟踪追击,设法要解开心中的谜团。
这是一户很普通的农村居舍,褐色的外墙略显陈旧,从门缝隙和残破的窗纸缝隙朝里望,只见吆吧和一位大姐在说话,这位大姐看来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两条粗粗的长辨很令人羡慕,但与人相比显得很不对称,听着奇怪的是吆吧居然改变了口音说的是和大姐一样的慈利话,立刻。聪明的我们马上就明白,显然吆吧是在冒充慈利人高攀上了慈利老乡,难怪一个人偷着出门。
恍然大悟后,我们也计上心来,决定由方玉来说慈利话,只要能攀上老乡肯定少不了撮上一顿饭,何乐而不为呢?
方玉也不推诿,于是三人便跨进了土屋门,直奔堂屋,把正在说慈利话的吆吧吓得从座椅上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她气愤地质问我们:“你们来搞么得”方玉沉住气说:“我们那么来不得呢?都是老乡”,听说又是慈利人,慈利大姐就问我们:“你们是慈利那里的?”方玉说:“我们是东岳灌的”,大姐又说:“我是猫儿峪的啊,离东岳灌不远啦,来来来,都来坐......”(听着方玉和大姐用慈利话对答如流,我和罗曼不会说只好躲到外面捧腹大笑),见到大姐那么热情,既然都是老乡是慈利人,此时吆吧也一反常态显得大肚容量和方玉相互配合,用慈利话拉着家常,而我和罗曼不会说慈利话又怕露馅只好少说为妙。
聊了一会,慈利大姐说有事要到公社去不便留我们吃饭,话音刚落,我们可冷了半截腰,哎!浪费了我们的表情,接着大姐又说:“我拍了一盆甜酒,你们吃吧”,听说有甜酒,我们又来了劲,涎水从口里一涌而出,但又假装斯文说:“不吃、不吃、这么点甜酒我们吃完了,你们就没有了”,大姐很热情说:“没么的,没么的,吃完又拍啊”,说着大姐拿来碗就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并说道:“都是老乡讲么得客气啊”,而我们也毫不客气的一饮而尽、一扫而光。
谢过大姐,吆吧和我们一同牵着牛回知青队,一路上吆吧很神气的炫耀着:“今天不是我的话,你们是不可能吃上甜酒的”,“那确实”,“不是你的话,我们不可能攀上慈利老乡,你还是有狠,俺佩服,要不在知青队永远也吃不上甜酒”。
说着、走着,走着、说着,就这样我们的关系又和好如初、重归于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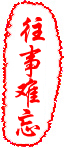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