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我的“战斗”我的“队”
从井冈山回来后,学校里已经是风起云涌,热闹得不可开交了。在校的六届学生,成立的组织不下100个,人多的几十上百,人少的三五两个。大家都以巨大的热情,疯狂的野心或者现实的利益打算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战斗队,企图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里依靠组织的力量弄潮戏水青云直上或者站稳脚跟保护自己。
在社会上,三大阵营早已成型,以“长保军”为代表的“保皇派”已渐呈颓势,以 “湘江风雷”、“红旗军”、“东方红”为主体的“造反派”锋头正健,以“高司”、“工联”为主角的中间派正蓄势待发。各派都有自己的宣传阵地,骂战秀才,大字报铺天盖地,最新最高指示天天出炉,省市党政机关基本瘫痪,“夺权”已经成为最时髦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班几个玩得好的同学(都是家庭有点问题的),平时都认为文革与己无关的,这时也有些蠢蠢欲动了。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
碰巧有一天我到姑姑家,看见表哥挺神气的样子,左臂上戴着一个鲜红的袖章,几个毛体字“湘江风雷”赫然在目。表哥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他现在是“湘江风雷”学生战团的司令,正在各中学大力发展组织。
我的这位表哥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他有时随便装出一付小布尔乔亚的潇洒模样,就可以使我佩服得要命。他做的事我绝对支持。
我做的事他们也支持。有人稍有疑惑:听说湘江风雷都是街办厂子里的人,是不是——我说,我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反正我们是学生。于是我们班的这几个人摇身一变,就成了“湘江风雷”在长沙市二中的唯一一支战斗队了。
既然成立了组织,总要取个响亮的名字吧。我们几个人冥思苦想,搜索枯肠,最后我说:“用鲁迅的句子:怒向刀丛觅小诗,就叫向刀丛。”
他们问:“为什么?”
我说:“我们要有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上刀山火海的勇气,而我们的武器只是一首小诗。”
他们都点头说:“妙!”
我们向学校申请住址和经费。学校给了我们一间教室,一台油印机,一令白纸,一叠红绿纸和毛笔墨汁等,没有钱。我们高高兴兴地把东西搬进了我们的地盘。
还差一样:招牌。
学校里两眼一瞪,没有。
没办法,我只好把家里的床板抽出来一块(当然是瞒着妈妈),六尺长,六寸宽,六分厚,刚刚好。拿到外面油漆、写字,终于挂到了门口:
“湘江风雷学生战团向刀丛战斗队”
谁是队长?我。
我对妈妈说,我会很忙,晚上经常不回家。妈妈将信将疑,又有点担心地帮着我包起了一床被盖。
就这样,“战斗”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当我们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找不到“敌人”。首先,我们对学校里的事情本来知之甚少,对领导基本上都不认识,何况领导们早已被打倒,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对学校现在的“阶级斗争”形势完全摸不着头脑。真正控制着学校的是高年级的学生组织。
社会上呢,“阶级斗争”又太复杂了,谁都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你批我,我批你,到底信谁的呢?我的直接上司即我的表哥倒是威风凛凛,“司令部”里有几个女生,都是他的崇拜者,他和她们眉来眼去的,有时简直就没把我的存在当回事。也难怪,表哥比我大五岁,那几个女生(她们是学生战团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也都有十八九岁了。
当然,在“司令部”的组织下,我们,主要是我总算到马路上贴过一两回标语,内容不外是“打倒走资派”、“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类,落款是“湘江风雷学生战团”。但这种事太没劲了。以后,我就懒得去了。
所以,我们没有斗争的目标,整天不知道干什么才好。我觉得自己比阿Q还不如,阿Q“我要革命”的时候,还可以欺负一下小尼姑,我们总不能去欺负低年级的女生吧。
我们也不能欺负无拳无勇的老师们。
我们心里其实并没有仇恨。
我们空有满腔“革命”热情,却无用武之地!
不过,恰好我们几个都是喜欢音乐的人,终于让我们想到了一件可以干的事:刻印歌本。
我们收集现在流行的语录歌、藏族歌、朝鲜族歌,用学校给我们的钢板蜡纸油印机,刻的刻,印的印,订的订,歌本出来了,但是质量太差,令人扫兴。看着这一堆废纸般的歌本,刚提起来的兴趣又跌落了。
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然后集中乘车到了机场,原来是迎接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只见湖南省歌舞团的乐队也来了,我的注意力马上转移到他们身上,眼睛死盯着他们手里的乐器看,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念头:要是我有一支这样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小号…)就好了…
参加“湘江风雷”一段时间,总算看见了一回“总司令”叶卫东。那是我跟着表哥去总部(设在湖南旅社),忽然听见有人小声说“叶卫东来了”,一转脸就看见了他。这位一中的老师披着一件呢子大衣,个子不高,表情却是一付睥睨万物的样子。他身前身后簇拥着一大群随从,我看见表哥有些讨好的笑脸。这是叶卫东的时刻!他的组织有几十万徒众。我突然想,如果给他戴上一顶三角帽,他简直就是拿破仑啊。
空虚和无聊攫住了我们的心。所谓的“向刀丛战斗队”没有战斗也不成其队,只不过是我们几个同学聚会的由头,而我们聚在一起时却无事可做。打牌下棋打篮球这都不是事。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2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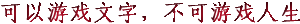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