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凡人生琐屑事
永兴一中退休教师 邓基柄
“人生苦短、岁月如流”,上了年纪的人普遍都有如此感慨。今年我已虚度八十四岁,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像走过一条路似的,也如一条河流过似的,虽然平凡,倒也回味无穷,谨分述如次。
一、童年少年时期
我生长在永兴县樟树乡树头下一个偏僻的乡村——枫头村,那里原先是樟树成林,浓荫如盖,纵横十余华里的村村落落,都有古樟耸立,故名樟树乡。我村前后除樟树外,还有两棵参天的枫树,春夏之际,浓荫如盖,喜鹊在树枝上筑巢,老鹰在枝顶上了望,好一道田园风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质困难时期,老乡们没有饭吃,饿不过,将古樟全部连根砍伐,熬樟油出卖换粮食吃,所以现在古樟已荡然不存。村头的两棵大枫树,因当地某人认为有碍他起的新房的风水,用一种烈性毒品钻入树心中药杀枯死了。多好的两棵大枫树,春夏葱茏可爱,秋天叶红似火,冬天披雪挂冰如玻璃,点缀我村一派美好风光,却被迷信风水的思想败坏了,现在回忆起来,深感可惜。
我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农村妇女,勤俭持家,虽然当时家境算是富裕,因我父亲是一位宿儒,也可说是书呆子。在当时永兴县第三高等小学当教务主任,长年累月不在家,只顾自身潇洒,靠我母亲操持一切家务,并从事农活。我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小弟弟还是襁袍中,我父亲就英年去世了。少年时的我,就得帮助母亲挑起沉重的家务担子,和母亲领着幼小的弟妹相依为命地度日。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永兴三高停办,一九三九年其校产分到所属各乡办中心小学,此时我刚高小毕业,后来(1941年)父亲也因抗战需要,由教育界转入政界,担任永兴金安乡乡长之职,1942年3月,在任内患重病不治而亡。父亲死时我年仅16岁。次年我初中毕业,不得不辍学在家,向族中长者求情,聘任我为邓氏宗祠国民初小教员,在此一段时期,我除读书,教书外,课余或假日,还要待好弟妹,遇春日翻地下种,夏日耨田,秋日收获,冬日砻谷子、舂米等劳动,没有时间玩耍过,失去我儿童少年时期应有的欢乐和玩耍。
二、求学生活。
我孩提时入本地邓氏宗祠国民初小读书,记得我的老师是一位穷儒叫邓国怡先生,本乡界江大队石桥村人士,国怡先生是当时农村一位饱学之士,从《三字经》讲起,一直教过我《幼学琼林》及当时初级小学教材,并教图画手工,体育、珠算、唱歌、游戏等课。先生很喜欢我,我当时穿的裤子是幼儿开裆裤缝紧的裤裆,做游戏时蹲下来裤裆就挤破了线,多不雅观,先生特意到我家要我母亲给我做一条新裤子……这些事我现在尚记忆犹新。
我小学毕业后,1941年考入永兴县立中学(现在的永兴二中)就读,时正值抗战忧患时期,日寇由长沙、株州、衡阳向永兴逼近,人心惶惶,此时我父亲于1942年3月病逝在任内,少年丧父的我仍未停学,艰苦继读。原省立衡阳女子中学更名省立三中,从衡阳迁到永兴办学,永兴沦陷后又迁入到蓝山县与其他流亡学校合办为省立联中,抗战胜利后(湖南省教育厅颁文指示湖南省立三中改名为永兴一中,所以县立中学后来改为二中),为了躲避日寇空袭,县中也从县城搬迁到乡下——太和圩寺边学校(原县三高小校址)办学上课。我为了节约伙食费,寄宿于学校附近一位农家,从家里带来咸菜送饭度日,咸菜放久了,起了蛆虫,我仍吃着它送饭饱腹,以苦读为乐。还记得在县城就读时,我的语文老师叫许清琦,那是1942年(民国卅二年)秋天,盟国援助我国抗日的三架美国战斗机因迷航,被迫降落于永兴县城便江河沙洲上,当时正是暮色苍然,天空微有月光,当三架友机飞近永兴县城绕城上空时,首先被省立三中师生发现。一位英语老师周老师高喊:“是三架美国战斗机。”当三架友机绕城飞翔。最后降落沙洲上时,省立三中师生云集沙洲进行援救,其中一架因撞上高压电线起火,师生们捧着河沙拼命救火,熊熊大火被扑灭,救出了受重伤的一位飞行员,其余两位盟军飞行员安然无恙。当人们正在踊跃围观之际,永兴县一位矮胖的艾县长拿着手杖(司蒂克)昂首阔步地在护卫人员引导下也赶到现场,因为他急于挤进人群,希冀用手杖打出一条路来,竟打伤了省立三中一位国文老师朱老师,因而引起省立三中师生的愤慨,其中有雷任同、夏士金、董源三位学生策划一次殴打艾县长的事,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幸而省立三中女校长周俟松(作家许地山的遗孀)主持正义,保护老师和三位学生,经省教育厅、民政厅派调查团调查调停,将三位学生作转学他校的处分,才免于事(见一中八十周校庆回忆录(P170-174《周俟松校长》一文,校友台湾国立高雄师大教授李雍民作)。我当时在县中读初中二年级,目睹此事,写了一篇作文叫《友机落永记》抒发了我抗日爱国的感情,许老师将这篇作文在学校广为传颂,啧啧称赏我这篇文章,并向县报推荐。
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去世,无力升学读高中,回家当了一期初小教员,以赚学费升高中。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省立三中于1946年重新迁回永城招生办学。我记得升高中考试的语文作文题是《凯歌声中度新年》,我以较好的成绩考上省立三中读高中,在高十一班就读。此时我家不幸遭了一场横祸——伪金安乡乡长曹学渊清算我父亲在世时任内有一批由乡政府负责向殷实户派购回的积谷款未购回积谷归仓。他硬说是我父亲生时在任要负责的。派兵丁到我家催缴此款,三天出两票,催款兵丁在我家打鸡杀鸭,吃喝足了,还要出差钱(当时叫草鞋钱)。此事实属乌有,因为谷款并未在我父亲名下,我父死后无凭证,由此我家横遭此祸。当时正值战后人民生活很苦,米贵如珍,饿殍遍地,为偿还父亲所欠积谷,年关时节,雨雪纷飞,我寒假回家,没有雨鞋穿,光着脚丫在雨雪中奔走,筹资购谷偿还乡政府催缴的积谷,当时我母亲一听村里的狗叫声,吓得和我四弟妹就抱头号哭,以为是乡政府兵丁催缴积谷来了。
当时惨像,不堪言喻……
我家为偿还积谷,母亲再无力送我读高中,但我不甘心寄人篱下当宗祠小学教员,只得从省立三中转学师范学校,一九四七年春我又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公费生就读。当时正抗战初捷,汽车火车尚未通车。我入学时,自己挑着行李步行百余里,天黑了不住客店,露宿别人屋檐下,天一亮,赶早到省立三师(今郴州市白鹿洞)入学。
1948年暑假在家遇到一桩趣事。那天我从田里干完活回家,见一位北方来的游方术士,牵一匹骆驼,叫着“看相呀!预知人生吉凶。”围观者一大群,我也挤在其中观看。看相的见到我后,拉着我手掌仔细看了一阵,说:“你不是庄稼人,是读书的人。你父亲早亡,母亲尚在,四姊妹,你居长……”说得真切,却没收我的钱。于是村人纷纷要求看相。至今忆之,亦难解看相之谜。
1949年上学期,我从省立三师毕业,先受聘于伪政府金安乡中心小学任教,接着迎接解放,又受县人民政府文教办事处新任校长何庆云女士(地下工作人员)之聘继任该校教员,学校地址在金龟乡的安福司。做地下工作的邓白、曹盛球、邓名国等经常在此活动,我曾积极协助过他们的工作,迎接家乡解放。
家乡解放后,我积极投入革命工作,参加过征粮,反霸镇反,土改,土改复查等革命工作,在这段时间,我先后在本乡湖塘完小,县内寺边完小任教,由于我教学成绩突出,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赞赏,1952年下期,将我从农村调入县城城关一小(现先锋小学)任教,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推广苏联凯洛夫教育教学教法。1955年下期,县教育科保送我以公职身份参加本届高考深造,当时被保送的共14名教师参加统考,高考揭晓后,我县仅两名——我和李长钦(曾任郴州师专校长,现已退休)被录取。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师院(现湖南师大)历史系带薪学习,被系里任命我为班上学习委员,兼任学院职工夜校的扫盲教师。
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席卷全国,在运动中我紧跟党的部署,立场坚定,得到系科党组织的赞扬,系科党组织派同志黄蒲生(浏阳人)与我谈话,培养我为入党的积极份子,因为即将毕业分配,就要我到新的工作岗位争取。1957年7月,我响应学院的号召,支援祖国西南地区的教育。我服从分配奔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民族中学从事中学教育工作,结束了我的求学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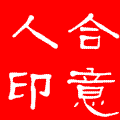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我的相册-
我的相册-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