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我们正年青。
——青涩的浪漫
往事缠绵,忽隐忽现,依稀又在眼前,翻身披衣下床,点灯寻物,却还是梦幻连连------。
黄旻眼睛近视,俩眼圆鼓突出,颈根粗大,扭头时整个身子都要转过来,十分笨拙。疑有严重的甲亢病,且又是独生子孤儿,按政策应不是“流放”对像,而那些街道的“良家妇女”,是如何将他“蒙,吓”下来的。黄旻一讲起这些“良家妇女”,气就不打一处来,脸红颈根更粗,夹杂满口骂娘的粗口不歇气。
黄旻虽是独生子,却无半点少爷脾气,人也随和,又极其忠厚老实,就是有点“抠”,月上西头,深山老林又无处可去。常一人躲在木板床的蚊帐里,先用口琴吹出震颤的,波浪起伏的“洪湖水,浪打浪”,使人想起家门口的湘江河,浏阳河,吹得你心酸酸的,待“洪湖水”平静下来,黄旻就开始悄悄的,轻轻的吃零食,还以为别人不晓得,对面床上的老孟有次实忍无可忍,对着蚊帐里的商旻大声吼道;你再这样唏唏烁烁,逗来老鼠,老子会把你的床掀掉,甚麽宝贝要躲在蚊帐里吃咯,真是碰哒鬼哒。
姐姐从城里给黄旻寄来一段华达呢毛料,那年月,这毛料可是稀罕物,蛮金贵的,黄旻却不以为然,女生们叽叽喳喳的热议着黄旻是做裤呢,还是做中山装,可都是笔挺潇洒蛮好看。可过几天赶集回来后,黄旻却带回几条内短裤,全由那段金贵的华达呢毛料做成,女生们顿时“花容失色”,扼腕叹息。黄旻却洋洋得意。
赶集买回的十几只小鸡,在大家倾情的关爱下,已长大成“鸡”,并开始下蛋。在大家精心的训导下,这些鸡们很有组织纪律,都是日出而出,日落而归,满山遍野,山丘田坎,全由它们扫荡,只只肉肥体壮,全不要你半点操心。第二年春节,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匆匆将这些鸡们处理后,只有一只黄花鸡婆未见归号,懒得寻找。便心急火燎的奔回潭城爹娘处。
来年几月后,又回到深山老岭时,打开大门,迎面便见黄花鸡婆从鸡窝里,咯咯而出,后面竟跟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鸡,煞是可爱,大家惊喜之余,才发现,原来黄花鸡婆在大门锁上后,还晓得每天都从双合大门下面的门缝处,钻进钻出,仍是日出而出,日落而归,十分遵纪守法,加上这深山老林只住着我们四男四女和一户农民,所以它安然无恙。而且它还安心的在这里“生儿育女”,堪称“鸡范”。
一日晚饭后,黄旻在八仙桌前,鼓着眼,神秘兮兮的悄声讲;老子今天在茅室棚里,用棍子戳死老米(邻居农民)六,七个小鸡崽子在粪缸里,出口鸟气,看他还总罩着老子啵。原来黄昏前,黄旻到茅室棚屙屎,发现这群小鸡崽,在茅室棚前“溜跶”,以为是老米家的,他和老米在干农活时,结过“梁子”,怄不过,耿耿于怀。于是在茅室棚里,解开裤子蹲在缸上,耐心的用零食诱导小鸡们到缸前,来一个戳一个到粪缸里。可怜小鸡都成了冤死鬼。
第二天打开大门,黄花鸡婆的后面,只有孤孤单单的二只小鸡崽,大家这才晓得;原来黄旻戳死的小鸡崽,都是自己家的鸡。黄旻看到后,半天不做声,俩只鼓眼也黯然无光。
黄花鸡婆每天仍带着它劫后余生的二鸡崽,日出而出,日落而归。
(二)
于是,大伙便簇拥着小猪崽回到深山老岭的家,猪栏就搭在厨房边,大伙吃饭时也能听到小猪的欢叫。小猪黑白相间,是当地土著猪种,来时已有三十来斤,十分“清秀苗条”,大伙一致同意取名“丽达”,简称“丽丽”,丽丽却蛮活泼好动,常翻过猪栏杆,到野外游玩,玩累了,饿了才记得回。有时搞得我们满山遍野去寻找,满山高唱“丽达之歌”,它才极不情愿的哼哼着回猪栏。
转眼又过了七,八个月,丽丽在大伙的“好饭好菜”的精心服伺下,长大了点,长壮了点,却总长不肥,抬着称了好几次,横直都是八,九十斤,大伙都纳闷;这只猪何解总长不肥呢?请来农大哥看看,他们都讲,这是只“米坨子猪”,长不肥了。再喂也是如此。于是决定将她宰了,炕成腊肉慢慢吃。
当把大锅架起,柴火烧起,猪栏里却不见了“丽丽”,大伙又只得扯起喉咙,满山最后一次高唱“丽达之歌”,好不容易将它捉回,它一看到熊熊柴火时,死活不肯就范,当小鼎亮出明晃晃的杀猪刀逼近它的喉管时,绑在楼梯上动弹不得的丽丽,两只眼睛分明流出了泪水,使劲摇着它黑白相间的小尾巴------。
丽丽走了,猪栏空了,它的躯体被分成几大块,当晚就放在灶上,准备炕成腊肉,年青的小鼎是个很心急的人,它将炕腊肉的灶眼塞满生柴火,因为生柴火烟特大,心想一晚就能炕成腊肉,便美美的去睡了。
半夜时分,忽听屋外厨房处,辟啪大响,且红了半边天,大伙这才晓得,厨房起火了,原来我们的厨房全由茅草搭成,火一碰就着,所有的人都立马翻身而起,端盆提桶打水救火,邻居农民老米挥着一把利斧,全然不顾火热,将几根屋柱砍倒,以隔离连房火势,因为厨房就连着老米和我们住的家。那一烧起来,便下不得地。火光中,只见他屁股后吊着只“尾巴”,原来他情急之中,只穿了一只裤筒便急吼吼的赶来,另一只裤筒就成了尾巴。那天夜里的大火,冲红了半边天,几里路外的村子都看得到,人们热议着火和丽丽,丽丽一时也成了那时的“火星”。
整个厨房连同“丽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灰飞烟灭了。事后才晓得,炕在灶上的“丽丽”,在柴火的高温下,满腔“泪水”(油水),往下滴,滴在柴火上,便真成了“火上浇油”,陡然引起大火,把整个“丽丽”热热闹闹的送上了西天。那只黑白相间的小土花猪,也只能在天堂听我们为它引亢高唱“丽达之歌”了。
从此后,再也没有养猪。
天阴沉沉的,刮着冷风,又好像就要“落水”(客家话;下雨)一样,王二爷的堂客哭着喊着告诉大家,昨晚在我家还坐哒蛮久,有讲有笑,还硬要把他欠二爷的十块钱还给二爷,二爷讲,手头紧,莫还着,他还死活不肯硬要还------。听哒二爷堂客讲,大家也想起昨天涞田时,和王四还打打闹闹,全然没有要“走”的迹像,怎麽一夜之间,喊走就走了呢。
在王四的书桌抽屉里,发现王四走的情因,他给二爷留下一封信,上面工工整整的写着;二哥,有130多元钱对不上账,是我把它花掉了,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大家,我无脸见人,只能一走了之。从信的字迹看,很工整清晰,证明王四走的时候,心里是很平静的。
王四自小读了点书,有点小聪明,由于粗通文墨,显得还老成持重,王四脸上布满麻子,背后人称“王四麻子”,人们总说“十麻九怪”,所以大家总觉得王四阴阳怪气,不逗人爱,二十来岁讨了堂客,没几年,堂客就离婚走人,崽也没生一个,到如今三十多岁,仍在打单身。其实王四虽然有点脾气古怪,但却还是个厚道之人,人硬扎,从不占人便宜。肯为朋友帮忙。尤其和知青讲得来,无事总爱在知青屋长坐不走,海策神聊。所以王四出殡时,队长王二爷指名要知青小马为他的四弟抬棺上山,小马念及和王四的友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出殡上山那天,八人抬的棺材很平稳顺利被送进墓穴,大家都讲,王四还是蛮有天缘的。王四从此便在那里安下家了。这是年青的小马第一次抬装着死人的棺材上山,蛮新奇刺激的。五年后,在潭城金井山冲里,小马又第二次抬着装着死人的棺材上山,且山陡路滑,却再无新奇刺激感,除了悲痛就是沉重,因为死者是小马被遣送农村劳改,老实可怜的年迈的岳父大人。
从此以后,再无第三次,小马也再不敢想第三次。
几天后,生产队查王四账时,核实王四用掉队上六十多元,并不是他所算的一百三十多元,六十多元就索去了王四年青的生命,年青的小马不由感叹;生命之短,生命之涩,生命之轻。
二十余年后,不惑之年的小马回乡看望昔日队上乡亲,王四那间老屋已撤掉,砌上了一栋二层楼的小洋房,整个村子已与当年是天上地下之别了。小马站在禾堂坪前,看着在王四老屋基砌上的小洋房,想起抬王四棺材上山时的情景,一时思署万千,感概唏嘘不已,他扪心长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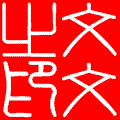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