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留痕(一) 军垦农场的大学生(2)
“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
春插终于忙完了,队上养牛的魏老倌因老家要修坟,向队长请了半个月假。这放养耕牛的事,就落在我这个专揽土松事做的人身上了。
放养耕牛是个比较轻松的事,只是责任重大,在当时牛是农民的命根子,看得比人还重。
清早,我赶着三头牛往岛口大堤坡上去放养。那里与千山红、军垦农场相邻。堤坡上长满了一种叫坝根子草的植物,是牛最爱吃的。
晚春时节,花红草绿。阳光照在堤坡上,把绿茵茵的草地映得发出绿油光。牛一到这里撒起欢来,贪婪地咀嚼个不停。
我先割了两担草,挑到副业队养蚕房边。用大粗瓷碗泡上一大碗老木叶茶。一边远瞅着牛群,一边和养蚕妹子调侃,好不惬意!
突然,发现堤坡上又多出了三头牛,定眼一望,只见离牛群不远的草坡上,一位带草帽的人斜躺在那里。
唉呀!比我还晓得享,抢到我的地盘上来了!我急匆匆地向堤坡上跑去。
跑到他的面前,只见他戴着一副厚镜片的眼镜,肩下垫着卷成一团的黄挎包,正聚精会神地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眼睛都冒往我眄一下。
“唉!你是那个队的咯?”
这位读书人头都没动一下,用眼睛的余光瞟了我一眼,目光又钻到那本书里去了。
我俯下身,用手拨了拨他头上那顶印有五角星的草帽。
“哎!问你是哪里的呐?”
读书人好象刚从梦里惊醒一般,摆正上身,取下眼镜,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擦了擦镜片,又慢慢地戴上,直愣愣地望着我,满脸的气恼。他不耐烦地用手向军垦农场方向挥了挥。
“哦!你是军垦农场来的大学生?”读书人点了点头,摘下草帽,从地上站起来。
我这才看清这位老兄的尊容,
“你是这里的?这几天怎么没见过你啊?”一张嘴就是一口京腔,看来早几天他就在这里了。
“我接魏老倌在这放牛,是长沙下放到这个队的。”我向知青组方向指了指。
听到这,他嘴角牵出一丝无奈的笑意,喃喃自语道。
“寂寂江山摇落处,恰君何事到天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向我递上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双手在身上乱拍,象是找火柴,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才弯腰在挎包里翻出火柴。手有点颤抖连连擦划着,点燃之后,深深吸上一口,又长长地吐出一股青烟。
“军垦农场那里都用机械犁田嗒!又养牛做什么?再说那边的草比这边好多了,我们这边都到那边去放牛,你倒是放到这边来了?”我噼里啪啦一通长沙塑料普通话追问他。
他点了一下头,慢慢道出了缘由。军垦农场作业一般是机械化,但有些农田泥太深,机器下不去,所以也放养一些耕牛,用于犁田耙田。他是北大历史系六七届毕业生,因身体痩弱,加之患有胃病、哮喘、神精衰弱多种疾病,学生连队就让他放养这几头牛。他把牛赶到我们这边来,主要是在这边可以读书,在那边让部队和学生连的人看到影响是不好的。
“小兄弟:借贵方宝地一用,多多海涵!”
他双手作揖,朝我摇了摇,煞有介事的学着京剧里的道白。
“哦!原来是这样!没关系,以后只管来!”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赶紧回答,一来二去我们闲聊起来。
“你是下放到此地的知识青年?这里的知青情况怎么样?”
我把下放的经历和这一带知青的情况说了一下。
“唉!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全家也和你一样。”
“你们全家都下放了,那是怎么回事?”我询问他全家的情况。
他又将一支烟燃起,烟力浮上头,思绪也随烟雾腾起来:他父亲是大学教授,是一位史学专家。文革一开始,就屡遭批斗,前年含冤去世。母亲也是中文系教授,现已下放到湖北孝冈X干校接受改造。唯一的妹妹高中未毕业也下放到陕北做知青去了。一家人是阴阳两隔,支离破碎。他说到伤痛处时,潸然泪下。
听到此事,看到此景。我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但连一点虚妄的安慰也无从开口,望着他神色黯然的模样,我立马上转移话题。
“你那是看的什么书?。”
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沾了沾眼里噙着的泪水,合上眼帘,久久叹出一口长气。“天理昭昭未许蒙,谁云屈抑不终通?”一字一句呤诵着。
也许流泪是一种疏导,他抹了抹稀疏的头发,脸色也显得开朗多了。
“呵!这是一本《旧唐书》,你读过吗?”
“没有,我以前只看过《隋唐演义》。”
“那是小说,应多读点史书,读史可鉴人、鉴己、鉴世。”
我点点头,赞许他的看法。
“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人,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说是吧。”
我茫然,本能的点了点头。说实在的,初中都冒读完的我,对于这些古训、哲理又何以说得清,道得明呢?只是觉得这位老兄唐诗旧词随口呤出,历史典故顺手捏来,可见他在古代文学和历史上面还是有些功底。
由于文革的来临,我书也没有读了,所以对这些读大学的人特别的佩服,对北大、清华的学子更是有几分敬佩之情。我向他询问北大有哪些学科,哪些知名学者等等,一脑子的好奇问题都恨不能一股脑地倒出。这位老兄跟我讲述了很多北大的旧闻趣事,让我得到些满足。
不知不觉肚子咕咕地叫起来了,该是吃饭的时候了。
“把牛都栓在桑树下,你也到我们知青组吃饭吧!”我真诚地发出邀请。
“罢,罢!我中午有它就可以了,只是忘了带水壶。”他摆了摆手,从挎包里掏出两只馒头。
“你去吃饭去吧,我帮你看牛。”他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赶忙跑到养蚕房,带来一壶茶水和一只大瓷碗给他。这位老兄见状,赶忙用手接了过去“实在不敢当!不敢当。”他抱拳作揖连声道谢。
回到知青组,我囫囵扒了几口饭,找XX借了一包烟,又赶快向堤坡直奔而去了。
下午我和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又聊了很多话题。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事物的看法立场鲜明,从不隐晦自己的想法。是个很直白的人。
“小兄弟,”他语重心长的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多读书,不断的充实自己,做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太少了。”
我听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夕阳西下,余晕缥缈,农舍上已炊烟袅袅。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背负农具匆匆往家赶。
我们都站了起来,吆喝这牛群往堤上赶去。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
郎此羡闲逸,怅然哥式微。”
这位老兄一边吟诗,一边用桑枝条抽赶牛群。
“读过晋陶潜的《桃花源记》吗?”
“上学时学过,不太记得了。”
“真羡慕陶公那种隐逸的生活啊!”他一声感喟。
我们把牛赶到渡口。让牛凫水渡过瓦岗湖,牛爬上军垦大堤,抖落身上的水珠。这时他也由摆渡的朱老倌送到了对岸,隔岸相望,我们挥手告别。
我站在堤岸上对他喊道:“明天老地方见!”
第二天我早早地赶着牛到了堤坡,一上午过去了不见他的踪影,我有点焦急起来。又等了他一下午,这位老兄犹如黄鹤,杳无影踪。到了傍晚时分,我心中隐隐的泛起了几分失落。正准备收拾离开的时候,看到队上的滴水老倌向我招手。他告诉我,他上午去军垦农场买东西遇见一位戴眼镜的大学生,得知他是从对面生产队过来的就赶忙撕开烟盒在反面写下了几个字托他捎给我。
我兴奋的接过烟盒纸,上面写着:
“小兄弟,春插已过,军训开始了,不能再过来放牛了,望多保重。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
XXX” 半年多过去了,有一天军垦农场放映朝鲜电影《买花姑娘》。我闻讯后和很多知青一起跑去观看。
我在军人服务部门口遇见一位熟识的大学生,向他打听起这位老兄的消息。他感叹的向我说起这位仁兄来。
原来这位老兄身体一直羸弱,军训时受不了艰苦的磨练,三天两头的请病假,躲在屋里看书。领导对他有看法,再加上他愤世嫉俗,性格执拗。每次学习讨论会上总发表不同的见解,难免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他。这样一来他像带了瘟疫一样,挨近他的人便人人自危,他也不愿意去影响别人,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孤芳自赏,郁郁寡欢。到后来发展到彻夜不眠,自言自语嘀咕不休。经部队医院检查鉴定为精神失常。
不久前,由部队遣送到他母亲下放的湖北x干校代管,并由他的母亲照料他的生活。听说已呆在湖北x精神病医院治疗。
我听完这番讲述,良久说不出话来,心里一阵凄凉,唏嘘不已……
请听下回“我这辈子交给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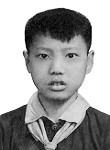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