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聚会马驹塘,与然哥聊天,然哥问我为什么好久不写点东西。一时无言以答,临时想出曾与人往来过几封信件的事,但担心这些内容与当下的快乐时光太不相干,所以只是私藏。然哥嘱我贴上来,说多点其他的声音也是好事。然哥是版主,而我的纪律性又很强,所以遵嘱先贴上我的一封。其实回信很耐看,只是没有征求回信人的意见,不能贴上。
这是我去年很意外地得到一本作者托她北京的朋友送来的她刚出版的书,内容涉及俄罗斯历史、政治、文化、艺术。惊喜之后阅读,读过之后感动,给作者写了如下一封信:
XX老师:您好!
首先感谢您的赐书。看过后真的很喜欢。喜欢您的文字,生动中含着引人发笑的机敏与幽默。有人说人生是一本书,反之亦然,我从您的书里看到了您丰富睿智的人生。
每个人都一定会有青春伴枕的书,我也有,也许很多与您的一样。从您的书里,我又看到了留在我青春枕头上的梦境:静静的白桦林,沉滞的伏尔加河流,克里姆林宫尖顶上闪烁的红星,宁静的乡村气息,带着月牙形头冠的俄罗斯姑娘,“金黄色的辫子垂在肩上”;还有临刑前的卓娅,记得我下农村前想得最多的就是她了,至少在我的青春里使我能在苦难中保持献身情结的应该是她和众多的俄罗斯英雄,也许苏联文学给我的学养比我们自己的还多;还有契科夫的忧郁,列维坦的忧郁,被那种忧郁浸润出的优雅也许给我们很多人日后的人生涂抹了底色,也铸就了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多美好的回忆,您的书牵着我的手在一遍遍地重走我的青春之路。我想,人生真正的财富就是美好的回忆,我们真的不能存下什么来,只有回忆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它象学问一样,已经长到我们身体里了。每天面对自己,都为自己高兴。就象我常常走在路上,老是不自觉地说几声“真好。。。真好”,回过神来反躬自问:什么事也没发生啊,有什么东西好呢?我想那就是心情。而那些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正是影响心情的催化剂。
想谈谈您的书:那幅伏尔加河边的两棵树的照片,浅酱油色的基调,让我想起了列维坦的《晚钟》,同样的静宓宁和。
最喜欢您对教堂的描写了,那段男高音的圣咏写得真好!从您的教堂里我好象看到了佐西马长老走过的那些地方。您的史料补了我似知不知似懂非懂之处。
在您的书中猛然看到《黄泉之上》,我知道的画名是《永寂之地》,一种很有力量的视觉冲击,一下子打到我心上。我很喜欢这幅画,说不出的感动,几年前曾写过看这幅画的感受,发给您看看,好吗?:
我喜欢列维坦的风景画,一幅《永寂之地》能看得你灵魂出窍。那无极的天空中垂挂着的云朵,沉甸甸的,包藏了对大地的冷酷无情,狂风将地面上一切人类的痕迹吹得东倒西歪,毫不在乎人类的存在。它在宣告,只有大自然才是亘古不变的。此时,在它面前你还敢说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吗?
不管是人是树是海水,是天空云朵,是日月星辰,我总能看出挥之不去的忧伤来,从画面里流淌出来的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不可知力的虔信,对生命的悲悯,叫你不由深深地低下你自以为高傲的头。
我还听过有人对这幅画作另外一种解读:从画家的那个视角看,这是一个刚逝去的人,灵魂正在离开这个世界,到了那个视点上,依依不舍地回头望着这块土地,——很有意思吧?我觉得是,很象的。这样的画看多了,就对人与人生,与宇宙的关联,总存一种恐惧敬畏之心。
我一直是忍着笑看您对新圣母修道院墓地的描述的,太精彩了。那些“意气相左”的人们最后还是在人生的终极目标上达成了一致,这真成了基督教中的一说“万物统一”论的一个有趣注脚了。
顺便说一下,我信基督教,我也喜欢追问那些难着边际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问题。我也时问自己,我的信仰之源从何而来?有时得出的结论之一,竟然是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有人说,俄罗斯是一个宗教情结很浓重的民族,即使是不信宗教者也仍然有宗教性的忧虑,俄罗斯人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俄罗斯人即使离开了东正教,也仍然会寻找神和神的真理,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常常想,这也许就是区别各个民族的特性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之一。说到这里,我还想请您看一段我与别人的对话,是您的书给了我胆气,让我在一个从未谋面的人面前敞开心扉:
再说一个原因——俄罗斯精神和民族性格。这是俄罗斯人愿意给《怎么办》这本书打高分的主要原因。如果在别的国家,这样的书也许没有如此地位的,可能只会归到“实验小说”系列里去。但俄罗斯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它老在思考一些对自己没有实际意义的很虚无的问题,它对人的关怀也是一种终极的关怀,面包总是排在精神后面的。也许各国都有这样的学者,但多是一家之言,扬个名,做个学问而已。只有在俄罗斯才会形成一种民族性格,那是从农民到贵族都会具有的性格。所以有人说“人人都在关心自己,只有俄罗斯人在关心大家”。所以他们才会整体都在关心“怎么办”。——那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我们可能觉得荒唐幼稚,但对俄罗斯人来说却是他们认为最好的最愿身体力行的了。所以这书才没被冷落。
这是我对《怎么办》这本书的看法之一,因为涉及到他们那个民族的一些特质,所以多说了。
您的书中对托尔斯泰的描述很精彩也很多,看得出您很爱他。我也爱他。他虽被开除教籍,但他还是个宗教信仰者,他与教会的冲突主要是在教会的官方化、世俗化与仪式化上。他与俄罗斯那时期很多知识人一样,是天生的良心体现者和道德至上者,“并且把人民看成上帝的直接显身”。这,是我用以区别与中国知识人的一个界线,我总对中国知识人有一种不算成形的看法:他们多以修身养性为美德,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点多在当下;而俄罗斯知识人更看重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是人的终极目的。不知您是否认同。
您对列宁的那几句叙述我很感动,确是如您所说,也许苏联的悲剧因子从列宁被暗杀后就开始萌芽了,列宁死前的心情一定会如您所述。再说我历来也很喜欢看这种先知性的表述方式。
您的书真让我很喜欢,(其实我想说爱不择手,但恐有客套之嫌),除了您优美的文笔、您广博的知识和您的机敏幽默外,我还很景仰您结构文章的能力。要把这样一篇既是游记又是史记又是人物传记,又有故事性、传奇性,又具知识性、说明性的东西写得这样美,把这些美丽的碎片接得天衣无缝,真的很难。我觉得您很独特,既不是直叙,也不是倒叙,也不是插叙。您是天马行空,让我们的眼睛象相机镜头,一会儿推远——与历史人物会晤,一会儿拉近——日前老百姓的生活埸景,忽远忽近,忽左忽右。明明随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但马上发现这地方我好象到过,不仅是那个虽然遥远却非常熟悉的年代,甚至是找到了我们自己曾在的地方, 甚至就是找到了我自己——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已经写得太多了,不愿过分打扰您,就此搁笔。再次感谢您为大家写了一本好书,也深深感谢您把它送给了我。
祝您好!
英夫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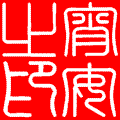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