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历程里的每个第一次,都是永远难忘的。在湖知网上看了好几位的回忆下放第一天的文章,都给我似曾相识的感觉,也给我不一样的感受。我不由得也想说说我们下放的第一天。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那个小城其实从文革前学习邢燕子、侯隽的时候,就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潮流。好像是1964年的某天,我刚读小学,看见几个大姐姐被动员学习邢燕子、侯隽,去农村,在街道居委会里一家人哭哭啼啼,难舍难分。1968年以后的知青下放,当然就是一股洪流了,所有的人只得随波逐流,否则,就要被“淘汰”。
1974年2月,我也要投身那个时代的洪流中了。 当时,福建一个姓李的人给毛主席老人家写了一封信,全国知青境遇因此普遍好转。我们很幸运,赶到了一个好时候下放。当时,知青办让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自主申报去向。下乡前,知青办组织下放同学集中办了两天学习班。在学习班,我和家住一个大院也基本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文武、祥巍、曲江、小果、郭飞六个人邀起来组成了一个知青小组。因为文武年龄最大,我提议推举他当组长,还表态坚决支持他当好组长,要大家服从他的领导。我们在学校时,几个人都各自有同学们互相取的诨名,什么“渡边”,还什么“酸水水”,甚至还有“土匪”、“屎毛陀”等等。在学习班里,我们起誓,从此后互相不准再叫诨名,别的不知情的同学叫我们诨名坚决不理他。知青办很早就通知了,把我们这个组安排到了当时全地区的知青安置工作先进单位太浮大队。
我对下放抱着很坦然的态度,车在离开县城时,我毫无牵念,不忧也不喜。我只是在车上思考,我决不能在农村过一辈子,怎么度过在农村的几年。对农村的生活生产,我是熟悉的,因为在母亲外出搞革命工作的日子里,在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挑大粪的日子里,我就是生活在农村祖父母、外祖父母家的,何况,我们在学校时还时不时被赶到农村栽秧割谷的。
由于在公社、大队几经转车、编排,我们到达知青点的第五生产队时,已是掌灯时分。五队的所有干部和一些老贫下中农,都来帮忙安顿我们。给我们做饭的是个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女青年,生产队长说,她是个高中才毕业的回乡青年。一年后,她入伍成了一名女兵,只是我后来一直没再见过她。
在昏暗的油灯下吃过饭后,我们才知道,刚才吃饭的这家就是我们的住户。那家男主人在离家很远的矿山工作,有两个70多岁多病的老人,三个小孩子,女主人好像不太讲究。我们六个人住一间漆黑的屋子,两个人睡张床,环境卫生很差,尿桶就放在床头,蟑螂到处爬。而与我们一同下乡到七队的女知青组和编入老知青一起的四队、三队几个组,住房条件比我们可好多了。当时说是临时住住,以后再给安排好一点的住户,结果,在那住了差不多一年,后来在我们再三要求下,才让我们住进了生产队的队屋,快两年时,县知青办拨了款,才终于给我们建了知青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生产队有空余房子的农户,要么是不愿意知青住,要么是有阶级成分问题,只有这家人男主人是当产业工人的抗美援朝老兵,也比较听生产队的话,把自家本来很紧张的房子腾了出来给我们住,还给了我们一间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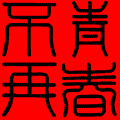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