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一个小故事。1948年10月,解放军逼近北京城(当时叫北平)。为了防止国民党败兵抢劫,农科院(当时叫华北农事试验场,地处城北郊区)留守处组织了一个护场队,由年轻工人组成,买了几条枪,护场。一日夜间,护场队发现有人翻围墙,就去看。“什么人?”“八路军先遣队”几个解放军战士翻墙进来。护场队队长姓杨,当时不到二十岁,听说是解放军,忙说:“我们交枪投降”就把手中的枪交给带队的解放军。为了能说清楚,向战士索要收条。那收条我见过,是一张粗糙的纸,上面用铅笔写道:“今收到杨某某交来**式步枪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纵*旅*团*连班长某某某。
几十年过去了,老工人小杨变成了老杨,退休后听说要落实离退休政策,按照政策,北京市清河以北1949年1月前,清河以南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可以算离休。就找到我父亲(当年的当事人之一)拿主意,我父亲建议他拿那张收条去问问,看有用没有。农业部人事司的官员见到这张小条子很感兴趣,让老杨交给“组织”保管,老杨听我父亲的嘱咐,坚决不交,复印件可以,原件一定自己保留。最后,凭这张收条,老杨和那一批护场队员都算离休待遇(从那天起算参加“革命”)。我父母因为保护贵重仪器、图书、物品躲避兵乱进了城,不符合离休政策,算退休。
这个小故事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说明政府工作人员是讲理的,只要确有其事,就承认,按政策办(当然非常时期除外);第二,说明“文件”的重要性。一张二指宽的小条,他具备了法律效力。不管过了多少年,后来的干部也得认。
近来网上关于知青园的修建方案讨论的热火朝天。我提出一个看法:应当确认该园的产权地位。其实,我当然不会迂腐到希望政府出示一张《产权证》什么的给我们。我只是认为,应当借此机会,明确这个园子的地位。按照一般的办事规则,修建一座建筑,应当有相关文件批示。如建设用途、产权归属、拨款渠道、经费来源、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许可等等。既然当年都成立过“办事处”,想必会有相关文件决定。希望雨晴查找一下:2000年是根据什么建设了这座“知青纪念园”(一般县档案馆应该归档)。如果(但愿)这个文件中规定了它的性质、地位、期限等等,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规定,甚至就没有这个文件,那我们再修建时就应当请示县政府,把我们的想法提出来,以文件、合同、纪要、协议等形式确定下来,具备法律效力。这样才能保证其永久性。不要想当然,认为一定是如何如何。不然,时过境迁,下一任或者某一任领导看着不顺眼,说K就可以K掉,那我们忙活什么呢?
说了归齐,就是要个承诺,书面文件,那怕是多少年后都管用的“小条子”。我相信后人会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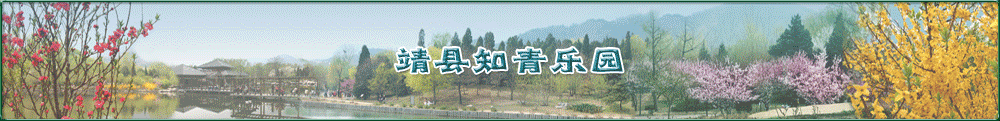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