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谁作的孽?
清晨,一队姑娘、妇女们睡意未尽的出早工去,那些来不及洗脸的还在用指头擦眼屎。连续几天的阴雨,清晨的能见度就跟他们讲的资本主义一样暗。
走在最前面的田家桃伢子(沅江将性别反着叫)突然发出一声划破长空的尖叫,随后拔腿就往回跑,后面紧随的十几位也不问原由,掉头跟着就往回跑。由于天暗,路湿滑,又唯恐跑后者会招不测,姑娘们个个连滚带爬的跑回队屋。
桃伢子弯腰驼背的曲着身,双手扶膝,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哈西港(虾须港)里——呼哧,丢了扎——呼哧,又白又胖的死毛貌(婴儿)呼哧,被港子里水泡的寡白发亮,两只眼睛鼓起好大!呼哧”“你还冇睡醒吧,我们队上又冇得哪家有嫩毛貌------”几个后来的中年妇女不相信地说着。一边朝哈西港走去,一个最调皮的妹伢子学桃那样尖叫了一声,这一叫把刚才那几个中年妇女的胆识叫没了,便折了回来参与到猜想联翩的队伍里来了。
知青屋离队屋近,消息自然传得快,我们都不敢去出早工了,缩回了被子里。年轻力壮的男社员扛着耙头过去了,他们把被水泡得鼓鼓的“嫩毛貌”耙上来,有人惊奇的叫到,这“毛貌”怎么长了条尾巴呢?哎呀!这是条小狗崽咧!接着,他们在港子里水草丛中相继又耙上来四只,真相大白了。我们在被子里听见社员喊翠萍伢子“你回克看哈你屋里狗窝咯”
那群出早工的妇女们,从惊变为乐成一团,又从乐变为气愤,各些贼X的青识知年作孽啊!
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在“敌人”眼皮底下有时又反而是最安全的。夜里,我们按二十几天前就商定的计划,将翠萍伢子家的狗妈妈逗开去,将窝里那刚满月的五只狗崽崽抱回家。听说广佬吃什么乳猪,我们冇别的,恰餐乳狗看,肯定大补。冇想到打开锅盖一看,滚开的水里那些还未开膛刮毛的狗崽崽随着开水在锅里翻腾,真的太像溺水的嫩毛貌了,十分恶心,谁也不忍再动刀。如是又安排知青满伢子——油炸,用撮箕装上五只狗崽,趁夜深且伸手不见五指扔到离队上最远的栏腰港去。油炸才走到哈西港,毛毛细雨加北风呜呜的嚎,又提着五只像死崽的东西,他越走得离队上远就越觉得害怕,那呜呜之声仿佛吹的不是北风是鬼魂在哀嚎,如是,他顾不得广大革命知青的高度信任,将它们扔进哈西港的草丛中,三步一回头的跑回队上,待我们睡着后才轻轻进了屋。
如今想起此事都感到愧对翠萍一家!谁要我们才17-8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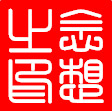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