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男人我的家
—人生不会像人们所说的那麽好,也不会像人们所想的那麽坏--
—(法)莫泊桑
(
秋天来到的时候,村子外头这幢土砖老屋却显得格外冷清,与村子里人们收获金秋的喜悦相比,这里显得有点凄凉,静悄悄的,几间旧屋都空荡荡的,已人去楼空,只有东房还有人迹,但也是破烂不堪,杂乱无章。几年前,三男俩女从千里迢迢的潭城来到这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就被村上安排住到这幢村外废弃的土砖老屋。他们被要求在这里扎根安家,几个伢妹崽口里也嚎着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要把他们最金贵的青春献给这冷清寂寞的小山村。几阵秋风刮过,几阵揪心泪水流过,三男俩女就只剩下孤苦零汀的知青梅丽,一个矮小瘦弱的女人。招工走了,当兵的走了,豪言壮语言犹在耳,却都成了过眼烟云,灰挥烟灭。梅丽实无处可去,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军统的父亲,退到台湾后,缈无音信,一直靠收破烂,打零工为生的母亲,也被政府遣送到湘西荒野山村,因体弱多病,不堪凌辱,实熬不过去,不几月,在湘西自缢而亡。梅丽得知此讯时,已是好几月后的事,连送终都未赶上。梅丽回到小山村这土砖旧屋时,已心冷如铁,人也变得痴呆木然。
梅丽是个平庸胆小的女人,平庸得你转眼就会将她忘记,只读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小学毕业生,十八,九岁了,还像未发育完全的孩子,一米五的个子,没有一丝女人的娇媚,没有一点女人的性感,“一马平川”的胸脯,虽有几处“小岗坡”,却与美女的爆乳蜂腰无法联想,一双混浊呆痴的细眼,常呆呆的望着远方。
只有梅丽无奈的留在这幢村外的老土砖屋里,她已无处可去,那年月军统的女儿,那个单位都是不敢要的,潭城除了一些远亲,梅丽也再没有家了。这幢风雨飘摇的老土砖屋,就是她唯一的家。
这个小山村其实不大,村里尽是何姓人家。民兵营长何华苟就是这村里的风云人物,当兵几年复员后回到这何家团,也算是混过江湖见过世面的人。因为自称是八代贫雇农出身,又和公社的头头脑脑“肉来酒去”,华苟在这何家团如鱼得水,独步天下。三十来岁的华苟,自出道以来,别无长进,沾花惹草却越来越在行,“何营长”瞄上的良家妇女,“连偷带抢",是难以脱逃的。仗着他的酒肉关系,大家都不敢做声,只好打脱牙齿往肚里吞。“何营长”开始百般关心瘦弱的梅丽,一双“鼠眼”老色迷迷的盯着她,评工分时,总要给她多上几许,时不时的到这土砖屋来问寒问暖,张口许愿;只要有机会,他定会尽力将她“推”出去,嘴甜甜的,百般讨好梅丽,梅丽一时也觉得这满口黄斑大牙的“何营长”,讲出人话来,还有点可亲可爱。
“何营长”搂着裤子,一边系着未用裤带的土布“三下裤”(注;又称扎头裤。寛大的裤头,往左右各折一下,再往中深扎一下即可,可不用裤带),一边轻声的抚慰着惊恐的梅丽,重复着他以前的许诺,睹着重咒发着毒誓,惊恐的梅丽静静的躺着,任其胡言乱语。
“何营长”心满意足的走了,村外头的这幢土砖旧屋,在暖暖的安祥静谧的月光下,显得格外温柔亲馨,小窗外安祥和谐的秋月,将她温柔的银光,投进这杂乱邋遢的东房,抚摸着瘦弱的梅丽的身体,梅丽静静的躺在陈旧的木板床上,仰看着土砖屋顶那被虫蛀坏的屋棂子发呆。
她被“何营长”掠去了一切,她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蚂蚁,随时可被碾死,踩死,她多想有个温暖的怀抱靠靠,让她喘喘气,歇歇脚。朦胧中,她忽然想起她死去的佝偻驼背孤苦的娘,正扶着拐杖,望着她眼泪长流,想起她蹣跚学步时娘的大笑,搂着她亲个不停,亲昵的念着;“丽儿哦,好崽崽-----”,想起她儿时在潭城那堆满破烂的家,发气时乱甩乱扔,娘的揾怒甛骂的表情。几行浊泪不由自主的顺着眼角,脸面汨汨的流下来,流到颈根,流到嘴角,涩涩的,凉凉的------。
(二)
转眼又到来年夏至,“何营长”的“三下裤”又在这土墙屋晃荡了几次,黄斑大牙的许诺已使梅丽心灰意冷,她只希望“何营长”的那些毒誓会兑现,她只虔诚的相信菩萨,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何营长”堂客极力的拉拽下,梅丽为了离开这恶梦般的土砖屋,离开“何营长”的“三下裤”,梅丽无奈的将自己嫁到了几十里路外的米村,嫁给米村的“白面书生”——米贵德,因是行三,又叫米三。梅丽终于离开了心悸心寒的土砖屋,有了自己的男人,有了自己的家。
米三因识得几个字,嘴巴又甜,在村里教几十个孩子读书,人长得白净斯文,米村的人都叫他“白面书生”。这“白面书生”其实是一阴险狠毒之人,他书生的“白面”,不知迷惑了多少人。
在洞房花烛夜时,正当他为自己能讨到一个“城里婆娘”而飘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花钱费力搞来的堂客,原来是一“二手货”,“白面”变成了猪肝色。一阵猛捶猛打之后,看似柔弱的梅丽却始终不开口说出“奸人”,她清楚这“生死攸关”的口开不得。她的另一个恶梦,从此开始。
米三还是天天勤奋的给孩子们上课,每天都是笑容可掬,逢人都客客气气,问寒问暖。“白面”总扬溢着浓浓的“善意”和“热情”。但经常到了深夜时,米三便开始折磨梅丽,把她捆在椅上,用毛巾捂住她的嘴,使力的在她身上掐,抠,打。在她身上无情的留下累累伤痕,留下他阴狠的情记。直到自己精疲力尽,方酣然入睡。天亮才让梅丽休息。
中秋节的深夜,在柔情似水的月光下,喝足酒的“白面书生”米三,将梅丽全身脱光,一丝不挂的捆在椅子上,用毛巾捂住嘴,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歇斯底里,用香烟在梅丽的乳房下,在她的小腹处,烙上了几个小小的“米”字,用心而工整,在梅丽白皙的皮肤上,十分醒目,望着这烙出的“米”字,望着梅丽滚滚而下的泪水,米三也含泪阴笑------。
每天,梅丽是第一个起床,搞好饭菜,按米三的规定,要跪着轻声叫米三起床吃饭,直到米三穿着齐整,梅丽才能起身,稍不如意便用烟头烫手烫脚。米三吃完饭梅丽才能上桌。晚上米三不开口叫她上床,她是绝不敢上床,不然一阵爆打又等着她-------。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米三喝高了酒,一阵爆打之后,米三一凳子甩了过去,正砸在梅丽脑壳上,她立时昏了过去。天快亮时,一阵寒风将她吹醒,米三正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梅丽觉得这个“家”不能再待下去,这个男人是个“索命郎君”,不如早点到娘那儿去,听娘念叨;“丽儿啊,好崽崽------”,她一下来了劲,爬起来摸到书桌旁,打开抽屉,拿出米三经常用的那瓶安定,一古脑儿的倒进嘴里------。
(三)
梅丽醒来时,眼前一片“白色”,戴着白帽和白口罩的女人,亲切的望着她微笑,轻声告诉她;这是在桃镇上的卫生院,你在这里已躺了一天一夜,你能醒过来,我们都高兴。梅丽是被米村的农民抬着一路狂奔送到桃镇抢救,是米三醒来后,发现躺在地上的梅丽已气息奄奄,立时惊出一身冷汗,连忙奔到几堂兄弟家里,央求他们赶快将梅丽送往医院。幸亏送的及时,加上那瓶安定也只剩下小半瓶,梅丽在生命的悬崖边没有坠下去,活下来了。医生在梅丽身上发现累累伤痕,其惨状都使她们噙满泪水,充满同情,在妇科检查中,她们还发现梅丽已不能生育,也是含泪告诉躺在病床上的梅丽的。梅丽得知后,放声痛哭了几次,为自己失出了人生做母亲的权力,痛心疾首,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痛心澈肺的嚎苦,让同病室的人也潸然泪下。
在被“何营长”掠出她的一切后,在被米三无情摧残虐待后,她都未像这样痛心澈肺的哭过------.
米三几乎每天都奔到卫生院来,在梅丽床前,捶胸煽脑,泪涕横流,“忏悔”不已,他知道;没有梅丽的发话,他这“白面书生”也就会成“黑面囚郎”了。梅丽异常平静,她已心如止水,面对这个心如蛇羯的男人,她只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心念——离婚,远远的离开这头狼。
梅丽慢慢的好起来,和米三离婚的事也很快办妥,米三也被清理出民办教师队伍,从此离开了那几十个天天给他们上课的村里的孩子,又开始荷锄种田的日子。
梅丽没有了男人,也失去了家,善心的桃镇卫生院长迟秋大姐收留了她,让她以临时工的名义,帮医院打杂,做饭,在医院安顿下来。
认识老莫,全缘于机缘,梅丽还躺在医院床上时,桃镇无数善良纯朴的人都到医院看望苦命的梅丽,为她捐钱捐物,使梅丽涕泪满襟,感动不已。老莫是在黄昏时节,背着他的修鞋工具箱,一瘸一跛的来到梅丽的病床边,没有多余的话,抠出一大捧全是分角的钱,轻轻的放在梅丽床边,又一跛一瘸的走了。梅丽一时还回不过神来,但她记住了老莫那扑实无华的脸。
镇上的人只晓得老莫是广西恭城一小镇过来的人,他父亲因年青时参加了三青团,又任麽子文书之职,肃反时关在牢狱里病死。老莫二岁时因得小儿麻痹症无钱诊病,活生生地使他成了一瘸子,娘带着他从广西流落到桃镇,在桃镇人的帮助下,在土地庙的背面搭起了一间批杉小屋,母子俩在桃镇安下家,为了过日子,灵慧的老莫十几岁就学会修鞋补鞋,修单车补车胎。镇上人都叫他“莫皮匠”,真名倒很少有人记得了。莫皮匠为人厚道,从不与人计较,你实在无钱,他也笑嘻嘻的把你的事干好,搞得人倒不好意思。自娘去世后,老莫更孤言寡口,终日里难说几句话。三十好几的人,还单身一个。
桃镇逢二,五,八赶集,也是老莫最忙的日子,梅丽在给医院买菜的时候,总喜欢待在老莫的修鞋摊傍,为老莫干点零活,为他的那些捐给自己治病的“七分八角”的善心还情。她好喜欢老莫的沉稳无语,常莫名久久的盯着老莫黝黑倉桑的脸,不愿离去。因为米三的冷血无情,使她觉得老莫的沉稳无言是一座可依靠的大山,这才是她心中依恋的男人,虽然老莫还是个瘸子,可在梅丽心里,却已是一个伟岸男人。在一个细雨菲菲的夜晚,梅丽不理会老莫的催促,不肯回医院,憨厚的老莫仍不知情理,准备送梅丽回家,梅丽一把扑在老莫寛厚坚实的胸膛里,轻声柔情的说;我要嫁给你,各就是我的家------。
在迟秋大姐的主持下,也就在这间批杉小屋,梅丽和老莫成了家。“莫皮匠”成了梅丽的男人。
在这称叫新房的旧批杉小屋里,昏暗的煤油灯下,老莫在梅丽白皙皮肤的隐私处,第一次看到那隐约可见的“米”字,听着梅丽倾情的哭诉,老莫心里如同大海呼啸奔腾,流着血,流着泪,久久不能平息。他仍无言,只久久的抚摸着梅丽颤抖的双肩,静静的抹去梅丽奔涌而出的泪水,心里在祷念着;梅丽啊,你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我老莫一定会叫你过上好日子------ 。
梅丽的好日子屈指算来,也过了十几年,这十几年对梅丽来说,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虽是粗茶淡饭,她和老莫却在无声中甜蜜的相望着过日子,老莫知道她不能生孩子,但老莫却深情的疼着她,依着她,口口声声;我的好婆娘-----,梅丽感到万分甜美,感到幸福。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她怨恨那留在隐私处,还隐约可见的“米”字,对不住她心爱憨厚的老莫,梅丽几次要用刀片刮去那可恨的“米”字,老莫都历声喝止,那可是梅丽身上的肉,老莫十分心疼。
一天已点灯的时候,仍不见老莫回家,梅丽预感不妙,心嘣嘣乱跳,当迟秋大姐来告诉她;老莫在回家的路上,一辆大货车将他撞倒,已送到县城抢救,只怕凶多吉少,梅丽赶到医院,流泪守着老莫一通宵,仍未留住老莫,临去世时,仍未讲一句话,只是紧紧抓住梅丽的手不松开------。
狗年的春天,乍暖还寒,梅丽来到她的胞衣之地——潭城已有年余,她已到耳顺之年,老莫已离开她好些年,她也恍恍忽忽的过了好些年,其间她被安排进了县建筑公司,离开她梦念的老莫的批杉小屋,尔后公司破产倒闭,只好应一远房表姐之邀,来到潭城招呼一年近八旬的老人——郭工,一位单身的高级工程师。郭工的儿子从美国特意回到潭城,以自己的名义购置了这栋别墅,将父亲接来居住,并委托梅丽表姐请来梅丽做保姆。在梅丽的尽心尽意的待护下,郭工深感梅丽的善良真诚,衰老的心倍感温馨,日久生情,在儿子强力反对声中,郭工携五十八岁的善良的梅丽,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梅丽很理解郭工的善意,从心底里感谢郭工在她晚年时,使她有了躲风背雨的家,一个栖身活命之地。
狗年中秋之夜,当一轮明月照在这冷清的别墅时,心情高兴的郭工,在和梅丽互贺碰杯时,突然抽憟中风倒地,梅丽心急火撩地叫120送往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医生说日后却得靠轮椅行走了。
这个中秋之夜
此时
2009--5-6--于星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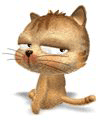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