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眯子流浪记
眯子在我们大队乃至全公社一直是一个闻名的角色,回城前的他闻名是因为他的才气与仗义;回城后的他闻名却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一种结局:今天的他竟成了一个令人一谈起就摇头一想到就欷歔不已的悲剧人物。事情还得从四十年前的下放时说起——
一
大下放那年,我们大队共下了三十多人(其中包括两户全家下去的七人),其中一个一米七高、戴着一幅高度近视眼镜的男知青非常引人注目,他就是以诗词歌赋著称、以琴棋书画胜人的眯哥,我们背后都叫他眯子。
眯子下的溪桥队与我下的生产队隔了一条溪,与他同队的是下放前住在他隔壁的新妹。新妹天生水灵,性格温柔,眼睛黑亮,与霓姐、雅俐及玲儿合称我们向阳的“四大美人”(我们大队知青首次聚会时,即将所有的男女老少知青“配”了对)。新妹虽没有霓姐那样文才;也不像雅俐那样开放,还少了一点玲儿的含蓄,但她独具豆蔻少女的羞涩美:在生人面前特别腼腆,尤其在男知青面前显得害羞,每逢与我们搭腔就脸红,但脸红却使肤如桃花的她更迷人!她母亲拜托眯子照顾她,可两人下到一个队后,眯子与她在生活上的不协调就逐步暴露出来了。
眯子称得上是一个文学青年,他读过许多古今中外名著,对中国古诗词格律非常谙熟,尤其擅长填词作曲。他不但文才好,口才也不错。另外的特长就是高音唱得好;笛子吹得忒动人;相棋也走得满有水平……可说是我们知青当中的一个能人呗!人的缺点也往往是随着其优点而来,由于他在家是独子,从小就有些骄纵,而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受到打击后,使眯子在文革前中学毕业后就流落社会。眯子慢慢竟养成了不修边幅的怪毛病,除此外在生活中他比较懒散,待人接物也不拘礼节;而貌若娇娥的新妹则穿戴整齐,虽然乡下环境差,但她仍然注意卫生,两人在一起开始还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凑合着,可时间一久生活矛盾加剧,柴米油盐具体,特别是每日的煮饭浆洗等家务活一落实到生活中,眯子与新妹就只能分道扬镳,各起炉灶,直叫我们旁人急得干瞪眼啦!
当时知青中有一个好风气:就是大多数人都爱看书。我们那里也不例外,我爱看西方文学名著,这样很快与眯子“情趣相投”了;与我下在一起的大个子喜欢下相棋,他与眯子经常杀得“难解难分”;另一个知青憨弟则喜欢听眯子讲《福尔摩斯侦探集》故事,所以眯子到我们队上来得多。眯子一来我队,还将其它队的知青引来。有一次来的人多,碰上我们只剩下一筒多米,于是只好将一个大南瓜和着一筒米煮了一大锅粥,七、八个人却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南瓜粥,憨弟留他歇宿讲故事,他讲到关键之处停下,大个子递上香烟后又开始。憨弟比大个子还爱听,我无所谓,因不少故事我看过书!已经半晚了,眯子的《三层楼上的钢琴声》讲了一半又不讲了,逗得憨弟从两层楼的热被窝里爬起,跑到两百多米的代销店叫醒店主,硬买了两包红桔烟回来,眯子才接着讲到天亮……
刚下放时我们还算过得下去,大队知青主要集中在杏花村的高军和霓姐知青组玩,多才多艺的眯子当然是主角之一。高军是一个会摔跤的美少年;霓姐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经常是在高军独跳“忠字舞”后,由眯子的清笛为霓姐的女高音伴奏,或者是他和能歌善舞的雅俐男女声二重唱……我队三个人都缺少音乐细胞,去了也只是跟着瞎起哄,那还真是值得回忆的一段“穷快活”时光呀!可自从头年双抢中大队斗争憨弟的大会被我们知青抗争而中止后,眯子也因是主要为首人而受到大队干部的记恨,他无法再在桃源乡下呆下去了,最后只得“走为上计”,干了一年多,次年迁到浏阳老家乡下去了。
但他人走了,他作的《月光照亮着杨溪河畔》的歌曲却永远留在我们胸中了:“月光照亮着杨溪河畔,晚风摇曳着山野花朵,吹来一阵阵暗香,我抬头询问月光,是否照亮着我的故乡……”我至今仍记得他春末离开桃源时给我留下的一首《调寄.临江仙》(赠友),其中上阙有“但恨识君晚,更何处觅知音?”之句,我因不会填词,只好用“何时相会难预料,悲感交加成高峰”之句敷衍他。
二
眯子迁到浏阳老家后呆了两年多,后来趁着照顾独生子女的政策回了城,随后抵母亲的职进了一家市绿化单位。
可他这个人也真是时运不济(据说他八字中的月份带“扫帚星”,极不吉利),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在难熬的乡村度过了五、六个年头的他,居然在回城后不久出现了意料不到的毛病:他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异常:先是语无伦次,接着脑海出现幻觉……他父母赶快将这个宝贝独子带往精神病院诊治,疾病曾一度得到控制。他母亲身体本不好,为眯子的病所急病又加重,好不容易吃药有了转机;她的右腿却又生了一个大浓疱,不久竟一病不起,乘鹤西去。他父亲因郁闷成为一个嗜酒之人,见妻一走更是以酒浇愁,丢下眯子任其病症发展。
眯子的病情一加重,上班也就“隔三差五”地迟到早退,单位本对他印象不佳,抓住这个机会要他“走路”。他生成的倔脾气,听到要他走人,竟然与单位领导大闹一番,之后不久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市绿化单位。
离开单位成为眯子人生悲剧的真正开始,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就与同公社的知青车宝合伙做书生意。在北正门租赁一个小门面,门面上没生意,他夏夜推着板车沿街卖书。有一天晚上碰到我,还送我一本,塞钱给他又不要,说:“反正要关店了,书全会送人呢!”
我望着他开始佝偻的后背叹了口长气,似乎预感到他未来的不幸!眯子卖书亏本后就重新犯起傻来,而且病状更厉害了。车宝不久告诉我:眯子开始对人说“有人要害他”之类的胡话(这是所有幻想型精神病人最初的通症)!而且越来越变得神经兮兮的,既害怕见别人,也害怕别人见他。“屋漏又逢连夜雨”——此时他的父亲也住进了医院,儿子不能照顾老子;老子更无法指望儿子了!
我对眯子“变疯”一直半信半疑,直到有一天我在蔡锷路的荷花园碰到他,便上去喊了声“眯哥”。他东张西望一下后,竟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莫和我搭白,有人跟在我后面“吊尾信”,要害我呢……”果然,他的神经中枢完全“断路”了。
我一听木然了,天哪!他难道真得了神经病,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越担心的事情偏偏越发展得快,几个月后他就完全“走火入魔”了。当时与他来往最多的某医院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眯子属于“文疯子”,即不会动手动脚去伤害别人的那种精神病人。他患上这种“幻想症精神病”后整天东藏西躲,害怕别人害他,担心会被人捉去坐牢……
已经从医院回家的老父拿了这个疯儿毫无办法,两个病人将一个家搞得一塌糊涂,连邻居也怕踏进屋去看了。凄惨的日子接踵而来,眯子的老父终于次年的大热天过世了,而眯子在父亲死了却还学着古代庄子在妻死后舞碟的情景:当我们赶去时,他正拿着脸盆在家中一个劲敲呢!最后还是眯子父亲单位处理了丧事。没有了父母的眯子无异于面临生命的末日,我们知青中几个以前与他来往密切的朋友开始资助没有一点生活来源的他,每个月给他送去几十百把元生活费。大半年后,他拒绝大家对他的支援,说他有新的生活“门路”了。
三
开始我们都纳闷:他的新“门路”是什么?不久即揭晓:他的所谓新门路就是出外流浪乞讨。一个活泼新鲜的生命忽然变成一个世人不齿的叫化子,反差太大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有父母,没有工作,没有健康的眯子开始了他后半生漫漫的流浪人生。他冬春季节是在星城的北端伍家岭至南端的涂家冲这条马路上沿途流浪;到夏秋时节又换到湘江一桥到新河三角洲沿河岸一带。第二年不知是遇到了什么人的“指点”,开始了一次流浪“远征”,他先沿路乞讨到北方那个乞丐成群的中原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呆了一年半载,听说由于他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开始在那儿还混了一个“临时”小丐帮头目,后来被当地的丐帮排挤只好打道回府,又回到湘江之畔的屋檐下。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有一天在湖南商场门前碰到刚回到故土的眯子,便走上前问:“眯哥,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说:现在好了,没有人再追踪我了,你也可以与我来往了。正当我觉得他已清醒时,他忽然说:“你有不有要我帮忙的事?我现在有许多关系。”我听后好不纳闷,就塞给他几十远钱说:你拿去买烟抽吧!随后离开了他。
我回家将此情形告知大个子,下岗已久的他说:眯子脑壳这个病是那回大队批斗会上挨的那一闷棒引起的。他现在睡在立交桥下,每天晚上十点后才归宿。大个子曾几次送衣物给眯子,都是在晚上去给他的。我知道大个子境况很差,他所在的厂子早发不出工资,年底仅发了一百元钱过年。他限于能力无法帮助眯子更多的钱物,也就尽一份知青的心而已。
在我们向阳大队的一次聚会上,几个知青都说到了眯子。小粒子第一个说:眯哥这辈子算是完了,我在芙蓉路上遇到过他,没有与他打招呼。
与眯子曾有过一段罗曼史的霓姐说:我在五一路十字路口一家饭店里看到穿着干净的眯哥坐在饭桌旁喝顾客剩下的面汤,我心一凉,吃也没吃就离开了。冬瓜弟热天则看见他在湘江岸边与人下棋……因为他在这个城市的四处流浪,我们大队不少知青都见过他一、二次,只是没有与他打招呼而已!
我注意到霓姐说起眯子时噙着泪花,那是发自内心的悲伤呀!因为她与眯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眯子在离开桃源前曾悄悄告诉我一人——那是眯子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青春往事:在那个月华似水的夏夜,两人一同散步到清幽的杨溪河谷沙滩上,肩挨肩坐在一块儿,聊着他俩共同的家庭际遇,诉说着乡下无边的苦闷。当月亮躲进云层后,他抱紧颤栗的霓姐,一阵热吻后将霓姐扶持到松软的沙洲绿茵上躺下,一朵羞涩醉人的夜来香在他惊悸的视野中慢慢绽开了……眯子说起那一幕毫不隐掩饰他得意的神色,他还炫耀:那是所有智者的语言文字都无法描绘的爱的极境,那是所有诗歌的华章都无法凭临的美的海洋,那是所有传统的栅栏都无法阻挡的原始欲望……
在戊子年雪花飞舞的寒冷冬夜,我和大个子站在五一路与芙蓉路的立交桥口,决心等待眯子的再次出现,与他见一面,可是等到半夜仍然没见到他出现。大个子说:眯哥的身体不知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呢?
我听后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脑海中倏地闪过一个画面:在大雪纷飞之中,眯子带着他对霓姐的那一幕难忘的美好回忆,蜷缩在立交桥下的角落里,身上盖着大个子送给他的那床被褥,安祥地合上了眼。他是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是带着对霓姐的深情,带着对知青伙伴的怀念,告别这个(对他而言)痛苦多于欢乐的人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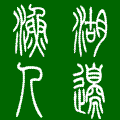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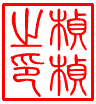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