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下放说起的辛酸
1968年11月28日,未满16岁的我。随着几千名知青下放到浏阳永和镇串石大队永兴生产队,插队落户,当时知青组四女三男(后来我姐为了照顾我)。于六九年初跨校来到我这里,到生产队旳头一天,我站在坪里哭,队长喊:妇女同志吃饭了;心里哭笑不得,一连半个月嗓子哭哑了。不管怎么样没有人在再我背后指指点点,骂我反革命子女,黑五类了,感觉挺好。
记得头一次砍柴,看到对面坡上好多干茅草,我们七人拿着砍柴刀,砍的砍,捆的捆,二人一前一后抬着往家送,干的可火热了,队上社员连孩子们都笑我们,他们都是烧松树,砍成一大块烧的,那么苐二天,我们就去砍大树了,一刀砍下去,怎么树出血了?听大人说是碰到鬼了,我们赶快磕头拜了后,继续砍大树,正当大树倒地时,队长等社员都跑来了,麻哩搞得这是棵桐树,队上就靠它炸桐油卖,我们齐说,这棵树已经死了,我们才砍的,里面还有鬼呢,我们把鬼都砍死了,你们看还出血呢?现在想起都想笑!那一刀给队上代来很大损失,几十年成材的桐树就这样被无知的我们而葬送。
我们利用国家拨款,盖自已的知青组,队长给我们请了位泥工师付,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开玩笑,泥工师付吃完饭会说:吃饱了;我们故意说:就不吃了;浏阳人很讲究语言,不吃了就是:死人就不吃了。晒衣服也挺讲究,男人的衣服晒竹竿旳大头,女人的衣服晒竹尾,我们偏不管,反着晒。这也是当地的风俗习惯,那时年幼无知,对不起了。
记得那时盖房子,筑到第九板墙时,框架空旳,泥工站在框架外等我担土往里面倒,而我粗心,一脚跨进去,只看到框架一翻,掉下去了,好在双腿分别在泥墙的左、右,脸嚓在墙土上又青又紫,低头往下看,一肆齿耙朝上,如不是双腿夹住墙摔下去,身上就肆个洞了,也没有现在的我了。房子盖好了,我们住进了新房,松树板做隔楼,一个堂屋,两边睡房,堂屋后面灶屋,茅厕,官渡二中的李钟南和毛大哥,光着膀子给我们打糞坑,被鸡死蚊子咬一身咜。
后来队长让我们喂头猪,我们觉得好玩就买了头猪喂,双搶的时候回到家中很晚了,猪饿的哇哇叫,还要给它先煮了吃,本来人都没饭吃,当时寻野菜给猪吃,肆个女的,我和我姐一组,柯叶和易新一组轮着做饭,记得我和姐姐寻猪草,有一种树叫漆树,叶子可以喂猪,但有人不能碰此叶子,否着会皮肤过敏痒的很,柯叶切猪草时,过敏脸肿的五官都平了,后来用九菜兜子捣碎抹在脸上,手上等处就没事了。当时农村兴端午节杀猪,每人只肆两猪肉,七人二斤捌两,那晚一个个等我把肉炒出来打伢记,可我不小心打开锅盖时将煤油灯打翻在锅里,这肉没办法吃了。那个年代酱油都没的吃,更何况肉、、、、、、可恨又可气又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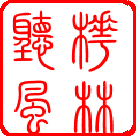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