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尘封的记忆
在我们家,老公除开‘卫生博士’的头衔外,还有个‘收藏家’的美称。有一次将我一条新买的棉裤收起,就怎么也找不到了。至今四年过去,后来又买的棉裤都快穿烂了,那一条还是没有找到。
但是,有利有弊。东西怎么说也是收在家里了,所以往往哪天又突然找出一样什么来,让你感到意外和奇怪!。
这一段时间,他天天看一个《开年鉴宝》的电视节目,不知触动了哪根筋,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象是在找什么,我也没有问他。
前天晚上,他告诉我,他自己的东西没找到,却帮我找了一件宝贝出来。我的宝贝?我有宝贝吗?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拿出个红皮塑料日记本,我疑惑地接过,似曾相识!
塑料皮上印着一个时刻准备歼灭来犯之敌的解放军战士。翻开看,封二又是三个背着枪,正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战士和民兵……
记忆的闸门稍微开了点缝,这还真象我的东西咧!
我赶快翻到扉页,清秀的字体跃入我的眼帘:赠给 耿桂琦同志 分别留念 愚友陈定德 75 7.28 于常德县断港头公社渔场
另外,还有一首赠诗(词)《采桑子》
至此,我想起来了,这是我招工离开时,渔场会计陈定德送我的。那首《采桑子》是他的大作还是引用了什么人的?我却完全想不起来了。
岂止是《采桑子》?这整件事都被我忘了啊!
记得去年参加沅江知青四十周年返乡活动时,曾采访了一位女知青,她保留了一本招工离开时各位同学、乡亲们题了临别赠言的小本子,令我非常地羡慕和感动。当时还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了一下,并没有想起这个红皮塑料本来!
但是今天,我突然就有了,有了一本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红塑料皮日记本,有了我离开渔场时一位‘愚友’的临别赠言。
多么宝贵!我得感谢我家的那位‘收藏家‘了!
在惊喜之余,又深深地自责:我怎么就忘记它了呢?被我尘封的仅仅是一个小日记本吗?
陈定德是和我同时来到渔场的回乡知青,但他的身份与我不同,他是公社派来的会计。据说他有个哥哥在区里什么部门当干部,因为有关系,他才谋到了当会计的差事。所以一开始我对他是有成见的。
但是渐渐地熟悉了以后,却发现这人并不讨厌,和我们下乡知青有不少共同语言,且非常同情我们下乡知青的艰难困境。经常不声不响利用职务之便给我们帮助。比如:最开始挑鱼池收土方,他怕我不懂行吃亏,悄悄暗示我留个高处的土墩收方用;打鱼草回来过称也常常多报几斤。总之,就我们知青当时的处境来讲,他还是够朋友的,留言上谦称‘愚友’确是名副其实。
虽然是‘友’,但因为他结婚生子比较早,与我们的接触自然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趋于一般。
但没想到的是,走的时候却只有他送了我临别赠言。
我想起,当时我还是非常珍重这份情谊的。到工厂后即开始用这本子写日记。所以这次将它翻了出来后,顺便又重温了刚进工厂时的生活与心情。让这小小的本子越发显得珍贵。
我想起,进厂后的第二年冬天,我曾回了一趟渔场,主要目的是去买鱼。其时渔场的领导班子已经更换。在听说陈定德没当会计而去看湖了时,我非常不解,还专门去了他看湖的地方赵家冲。
在湖边低矮的小渔棚里,我见到了他。依然温和的笑容,依然瘦弱的身材。原来常戴在头上的绿军帽不见了,却象所有的湖区农民一样,用一条长长的白毛巾把头部保护起来。
和他简短的交谈后,得知他来看湖的原因一是‘看不惯,和他们搞不来’,二是‘看湖路子活些,要不养不活老婆孩子咧’。
我想起,我告别那小渔棚时心情有些沉重,而他领着老婆孩子一直站在寒风中目送我离开……
尘封的记忆太多,几十年一晃而过!如果不看到这个小本子,我会有这么多的想起么?我无法回答。
油匠上次回乡,带回了渔场新面貌的照片,也带回了渔场已并入国营县渔场的消息。
我不知道陈定德是否还在那里,也不知道那四层的渔场家属楼,是否有一套属于陈定德?
我只知道,如果有机会再去断港头,我一定要打听他的消息,一定要和这位‘愚友’见上一面。
我期待着!
和韵 一首
《采桑子》
芦叶汀洲几入梦,冲天湖边,花样少年,雨打青荷枝叶残。
离愁寥寥有数行,重拾寄语,已逾经年,尘封记忆起波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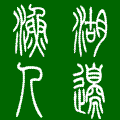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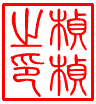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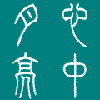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