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年的农村经历》
木林森
...... 夏初.丘陵山区的气象难测,五十年代在偏辟的山村,全凭老人们的经验,四季节气和民间流传的谚语而定.
芒种时节,天有不测风云,观山村的公社大食堂寿终正寝后,社员家仍旧各守炉台,自食取火过着老日子.
一风飚过,另股袭来.天空乌云黑压压翻腾,有经验的农把式知道夏至时节的暴雨将至.
当日.人们缩窝在家,自乐清平,难得清闲.忽然,“铛铛铛”的敲钟声急促响起,“铛铛”声比平日更久更响,从乡村旷野传来喊话声:“各家各户,至少去一人到祠堂开紧急社员大会啰,有重要事情宣告,那家不去人,扣工分啊!社员同志们,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奔向共产主义......”
观山大队在竹山湾村的靠山坳的石头坪,垒起了三座小土炉,通上风箱,将煤炭点燃后再续上废铁,土炉子开始冶炼起来.煤炭和柴木消耗很大,炉火旺盛,火光冲天.可就是炼化不开废铁,反而把土炉给烧塌了.经过了解,方知修土炉尚需耐火材料,于是就请来懂些炼钢技术的技术师傅.重新垒起土炉......终于把废铁烧结在一起了.因为是废铁与煤炭柴木混合烧制,炼化出来的“钢坯”都成为豆腐渣形状,比牛粪还不堪入目。
58年的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在乡村要铁砸锅,劳命伤材.砍伐森林,严重破坏山体植被.盲目快上,超英赶美.不是专业工厂,更不懂炼钢技术,如何炼出钢铁?岂不是天方夜潭。
五十年代的农村乡间,哪里经得起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的乱弹琴,折腾完亩产千斤,甚至牛皮吹到亩产万斤,一败涂地失败后.大炼钢铁运动的摇旗呐喊也停歇了.山坳的石头坪仍又成了我们孩童玩耍的乐园,我们年少虽弄不明白那些乱弹琴瞎捣鼓的缘由,心里还是十分明白:大人们的事干砸了,昔日冲天的牛劲变成了丧气的苦脸。
工农业齐步“大跃进”己成为历史,痛苦和灾难己经过去,但它带给人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大跃进”是一场悲剧,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才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地反思.
正值双抢时节,母亲临产.五十年代的乡村缺医少药,半夜时分,妈妈叫醒我:“强伢子快起来!”
妈妈急迫地叫唤着我,语音里带着呻呤。“快点噻,到叔叔那里叫婶娘快来,你就说妈妈肚子好痛,要生毛毛啦。”
妈妈捻大煤油灯,她的脸色惨白,脸上冒着泪珠,卷缩着身子倚靠着床头,双手抚摸着凸凸的大肚,不停地哼哼:“唉呦,唉哟!”……
我急忙跑出房门。夜空灰蒙蒙的,月光暗淡。我趔趔趄趄沿着小路摸到叔叔家,重重地锤打着叔叔的房门:“叔叔,婶婶,婶娘.妈妈要生毛毛啦......”
婶娘对叔叔说: “你快到九庙公那里去,请王婆婆,快点噻!王婆婆接生有经验,顺便叫声他满姨,”
大人们和接生的王婆婆在屋里忙得团团转。满姨揭开灶台上的木盖,倒满一锅水,麻利地点燃灶堂火。她招呼我把火烧好,丢下火钳,提着脚盆转进妈妈的房间。
天刚蒙蒙放亮,妈妈的房里传来一声嘶哑的毛毛嘀哭声:“呀吖,呀吖......”. 打破了宁静的乡间小屋.满姨满脸堆笑提着木桶走出房,边舀着热水边对我说:“你没能想到妹妹哟,妈妈又给你生了个弟弟,也好,在乡里不怕伢崽子多,以后出工有劳力,有个什么麻纱事,三兄弟往那里一站就是一堵墙,谁也不敢欺负你娘。”
小弟弟出生后,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总是感觉四肢无力。大热天额头上还缠着一块蓝色方格手帕,太阳穴贴着两块黑膏药。好一段时间,她一直吃着乡下郎中送来的草药,每每煞煮草药时,妈妈会反复提醒我:“快去看看,莫烧干水哒,小心,莫烫哒!”
吃不饱母乳的小弟弟整天哭声不停,妈妈总流着泪水轻轻拍打着怀抱中的小弟弟,喃喃自语“等你爸爸回来,我们就回趟城,到城里看医生,等妈妈病治好哒,一定会有奶呷,让你呷饱啊!莫哭莫哭睡觉觉啊!造孽啵,才三、四个月就要喂烂粑饭,呷煨竽头.”
那年月医疗卫生人才严重匮乏,公社卫生院设施十分简陋,卫生服务站只有“老三样”,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器,一个体温计。医疗卫生事业相当滞后,缺医少药,严重威胁农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乡村的农民得了大病,只有求助于江湖郎中和本地的土医生,农民“小病不用看,大病无处看”;小病等着好,大病拖着死;常常小病拖成大病。
我母亲生小弟时,受当时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所限,接生被感染,产后疾病不能急时医治,靠江湖郎中,土方草药久治无效,小病拖成了大病。
那年冬末,眼见妈妈一天比一天消瘦,说话有气无力,一日三歺进不了三两米,倒是草药汤每天要吃两大碗,白天中饭前一碗,半夜把留下的另碗草药汤,用沙罐放置地灶火栨灰里保温。上半夜我睡她的床外边,每到半夜,妈妈催醒我,我揉着挣打不开贪睡的双眼,从温暖的被窝爬起,妈妈总是叮嘱:“快穿衣,千万别冻着。你可不能着凉生病啊!你那死爸怎么还不回呢!?妈这身子也不争气,把你害得睡觉都不安神,崽欸!我的命真苦啊......”
妈妈的咳嗽声搅醒了小弟,嘶哑的哭泣声打破了平静的小屋,妈妈尽力从床里边抱起小弟,解开衣扣送入怀抱,见妈妈眼中含着泪水,我的鼻子一酸,跟妈妈说:“妈,满姨不是说了吗,不要老是流泪,流多了对身体不好,妈妈你莫哭啊!......”
看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我睁着模糊的泪眼,把一大碗药汤递给妈妈。“放到条案上,等下再吃。你去拿二块片糖来,这背时的药好苦呵!看看还有多少片糖,多拿一块罢。你弟是饿了,看来是没奶喂他,唉!” 小弟吃不到母乳,哭吵声越来越大,妈妈把片糖放到小弟的小嘴里,小弟立刻停止了哭泣,“叭嗤,叭嗤”地吸吮着,慢慢睡着了。妈妈放下小弟,掩了掩里边的被子。
“快上床,还是睡妈妈外边,莫把你大弟弄醒啦,妈妈想跟你说说话”。 我爬进被窝,妈妈抱着我,用手轻轻抚摸着我。她拿起一块片糖噻进我口中,片糖好甜。往常妈妈只掐小半块片糖给我吃的,今晚上,妈妈却将整整一块放进我的嘴里,我感到了妈妈对我的一种异于平常的爱。她好像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强伢子,妈妈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啊”! 妈妈喘着粗气,断断续续说:
“ 你是长兄!两个弟弟太小,以后好好带着弟弟啊,等你爸爸回来,跟爸爸到长沙去,乡里我们住不得,要好好读书啊......”“读哒书在自己的肚子里,贼都偷不走,火也烧不着”。
妈妈说话很费力气,泪水伴着呻吟。阴冷的黑夜里,妈妈将头无力地靠在我的手臂怀中,渐渐的,她没有了声息,她的头向外偏倒。一种不详之感笼罩着那间屋子。我放声大哭,用力摇喊着妈妈:“你莫睡啊,妈妈!你醒醒!我不要你睡啊,我记住你的话了,妈,妈妈......”
放在条案上的药汤凉了。妈妈没吃。我爬下床,端起药对妈妈哭喊着:“妈妈,你还冒吃药的,妈妈,还有好多的片糖,我听妈妈的话,我没有偷吃过片糖.”
妈妈偏着头一动也不动,她没能等到父亲回家就离开了我们。那年她才36岁。小弟周岁未满,大弟5岁,我10岁。
58年的冬天,特别地寒冷,天空飘着鹅毛大雪,爸爸解开棉大衣包着小弟,小舅牵着大弟,迎着寒冷刺骨的北风,顶着漫天飘雪......从青山桥陡步艰难地赶往花石长途汽车站,每日只有一趟的早班车至湘潭,行程30多华里.傍晚再乘车从湘潭至长沙。那时的客车还是在汽车尾部燃烧木炭,汽车棚顶上背个很大的黑色橡皮气囊。 冬天的深夜,拖着疲备不堪的身体,感觉长沙城似曾熟悉,跨进伯妈家的门,却又感到那样陌生......
一种空空的失落和伤心,让我回到长沙这个没有妈妈在身边就不是家的地方。忘不了也是最难过的,莫过于母亲患病时,整天盼父亲回归的痛苦表情,还有对父亲的那种思念。为妈妈做丧事过程中,父亲仰天痛哭,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大人撕心裂肺的悲嚎,他不断呼唤着妈妈,双手拍打着黑色的棺盖,要打开棺木见妈妈最后一面的情景,我似乎才明白,妈妈真真地去了,但她去了哪里?那晚的情形,常会让我空悬着双手,感到妈妈靠在我手臂怀中的余温,还有她轻声的嘱咐;盼不到爸爸归来的失望和无助,成了永远的遗憾和痛楚。
新的生活环境在等着我,我还能去学校读书吗?
我好想好想快快长大......
全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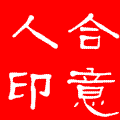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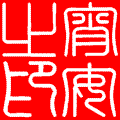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