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为聚会所作,发上一是献丑,二是增加家园帖子。
聚会随想
我是初二第一学期由24班调入23班的。由于班级相邻且同为田厂子弟,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
那时,尽管“阶级斗争”盛行的国度里已然刮起了 “四清”之风,同学们毕竟少不经事,整日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倒也开心。作为成年人的师者,可能会要承载一些政治的压力,转嫁到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身上也就见怪不怪了。
考试之余,好学者大都有趴在玻璃窗外偷看老师批改试卷的习惯。一次,我碰巧看见语文教师何乾象在批改我的题为《记一个老工人》的作文。临近上课铃响,正逢老师落笔分数。只见他朱笔在卷右上角一挥,95分的成绩就定格在我眼前。我心中窃喜,跑步回到教室
数日后试卷发放下来却让我傻眼:95被划去,下方的85也被涂改,排行第三的分数65却跃然纸上。我找到老师,不敢说是论理,也算是问个明白吧?何老也简单:你写不出这种阶级感情!我无言以对。
无独有偶,青年教师里也有喜欢拿捏我这个“软柿子”的。当我稍微心旷神怡,口吐妙语活跃于课堂之际,一声断喝: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劈头盖脸一阵痛批,直叫得我这个15岁的嫩崽体无完肤。
从此,只要是这个老师授课,我就在下面画画,结果自然是数学和作画均属“业余”。好在还有一些喜欢我的老师有如缪礼治,杨芳德,温靖华等,才没有荒废中学的全部学业。
自觉在同学之间没有远近,亦无亲疏。进入文革停课时期,倒是和程勇走得近了,我常常往他住的和平村跑。
这位仁兄受他父亲影响,喜欢钓鱼,行头一律自制,像模像样。我先前也在田心周边的乡里沟边转转,自从和程勇泡上了,也学着做“正规军”了。我们一起到农村偷砍竹子,燻制钓竿,自制的筒篙,手篙,一应俱全,甚至爬货车跑到长沙动物园偷豪猪背上的刺做浮漂。打那以后,我们总是结伴而行,逍遥自在几年。
68年11月28日我下乡浏阳的那天清晨,程勇捉了一条狗崽送我,让我成了株洲市唯一带狗下乡的知青。
图片分别摄于40年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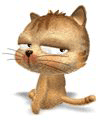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