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潮曾经迭起,知青都已老去。
1998年,两位曾插队内蒙的历史学博士,以时间为界,各著知青史一本(《初澜》、《大潮》),合称《中国知青史》,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学术著作十年前未能广泛传播,时至今日,98版《中国知青史》已是芳踪难觅。200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从故纸堆里淘出这段尘封的、属于知青的“无悔青春”再次出版。北大教授印红标指称,这是中国内地知青书里最好的一本。
中国的知青轨迹:
1954-1958:向荒地进军 =》 1958-1968:知青群体形成 =》
1967-1973:上山下乡 =》 1974-1976:曲线回城 =》
1977-1980:拨乱反正 大返城
中国知青史 • 初澜(1953 - 1968)
作 者: 定宜庄
出 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
定 价: 38元
ISBN: 9787801707833
出版日期: 2009.02.
版 次: 1
定宜庄,女,
1968年秋,北京10多个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被批准插队的中学生打着一面红旗,徒步前往锡林郭勒盟,以表达他们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
阿巴嘎旗白音图嘎公社前不久接收了一批知青,分到3个大队,乌格尔木大队没有分到一个,牧民很生气,队长跑到公社和旗里面去闹。徒步而来的知青在锡林浩特听说此事,赶到阿巴嘎旗,坚决要求去乌格尔木大队。经旗里批准,他们如愿以偿,牧民、知青皆大欢喜。
多年以后,《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定宜庄:“你们举着理想主义大旗上山下乡,我特别羡慕你们当年的激情!”她微微一笑:“我从来没有理想主义,插队的时候,理想主义早已被打得粉碎了。我从插队到现在已经非常厌倦这个词,这个词在我身上已经不适用了!”
定宜庄搬进了贫下中牧郝鲁洼夫妇的蒙古包里。“插包不是我想像的贫下中牧有多少优秀品质能跟他们学,可是我确实感到了一种亲情……”定宜庄坦言。每天早上,定宜庄去放牧,郝鲁洼亲一下她的额头和脸蛋,拥抱一下:“姑娘,天冷,出去小心呀。”额吉帮着轰出羊,搂过她来,抚摸一下头:“孩子,小心呀,早点儿回来喝茶!”“每天像举行仪式一样……”定宜庄难忘这份亲情。在她知识分子家庭里,是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如今,她也会用这种方式对儿子和学生表达亲情。
“我当时一个特大的理想就是上医学院,毕业后当医生!”机会很快来了,自治区招收工农兵学员,她被牧民推荐到内蒙古医学院学习,审查很顺利。牧民为她送行,纷纷送来奶食品……但是,入学通知书迟迟没有发下来。“我急了,你想呀,当大学生和在当地插队当一辈子农妇,有天壤之别呀!”定宜庄跑到旗里询问,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定宜庄找到盟里,一位提干的知青是她父亲学生的孩子,他说了实话:“你别找了,也别问了,你的名额被粮食局长的姑娘顶替了!”定宜庄学医的梦想就这样被打碎了!
1974年,北京在内蒙插队知青中招收中学教师,这次总算如愿以偿,定宜庄回到了北京。之后,教书,结婚。1977年,恢复高考。定宜庄领了报名表,但是孩子刚出生,她只好忍痛放弃。意想不到,半年之后,又有了第二次高考。“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放弃了。”定宜庄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看书,上班路上,回忆所看的内容,到学校再看一遍。上课最后10分钟,学生做题,她跑到教室后面看地图,记地名。做饭时,书就放在旁边,见缝插针地看几页……高考成绩下来,定宜庄在海淀区名列前茅,1978年,定宜庄终于圆了大学梦,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得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硕士学位,1991年,攻下了历史博士学位。1993年,定宜庄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有记者问定宜庄:“作家写了那么多知青作品,你为什么现在才写知青史?”她说:“因为历史是学术,10年才能成就一个史学家,文学家靠感性,所以常常走在史学前头。”定宜庄说,多数知青当年上山下乡没有选择,是完全被动的,境遇很悲惨,首先是没有文化,有几个人有机会上大学呀,大部分奔波着找工作。“我们有知青的阅历,拿到了
中国知青史 • 大潮(1966 - 1980)
作 者: 刘小萌
出 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
定 价: 62元
ISBN: 9787801707840
出版日期: 2009.01.
版 次: 1

刘小萌,男,河北完县(今顺平)人。
“大潮涌来——几千万少男少女的黄金年华卷进了黑泥黄沙红壤,山川田野莽原。”
1973年,初中文化程度、在内蒙插队5年的放羊倌刘小萌转回河北保定原籍,在完县(今顺平县)当起了农民。从牧区转到农村是没问题的,那边是放羊,这边是种地,都属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范畴。一年以后,刘小萌当上了生产队长。外来户能在农村当干部,一是因为知青有文化、能吃苦,二来没有社会关系,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干。两年后,刘小萌被县里推荐去了保定技工学校。此外,离家近了,当时保定“武斗得乱哄哄的”,坐火车不用买票,刘小萌居然因此回了7次北京。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刘小萌“根深蒂固地想上学”,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刘小萌考进了河北大学历史系。数理化荒废了那么多年,学理科是没法想的了。学中文的父亲建议子承父业,他不情愿,一心想离政治远点儿,“文科里面,历史离政治最远。”他压根没想到,十多年后,他又会在清史之外,自觉自愿地研究起知青史,一下子把自己重新纳回跟当代政治无法剥离的境地。
因为研究知青史,刘小萌在原先的科研队伍里一度受到排挤,成稿的论文和书稿也迟迟不能付梓,同时,他还不能荒废本身的专业。“我当时是副研究员,专业上有压力,评职称那会就特别忙,天天熬夜,4个月写了40万字,那时候还没电脑,全靠手写,手老麻,后来凭借着论文《爱新觉罗家族全史》评上研究员,庆幸没耽误。现在我隔几年就拿出一段时间来做知青研究。我老在反思,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利用环境来做点事。起码,在知青史上,大的问题、大的事件目前还没有没写出来。书稿不能及时刊发其实也是好事,放在那里就会老去修正它,希望它能尽量减少局限性。中国当代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但是知青史这一块,现在我们跟国际上还是接得上轨的。”因为不接近学术主流、长期独来独往,同事管刘小萌叫“独行侠”,他自己苦笑,说大概是当知青时放羊的潜在影响,强化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学术上边缘化,和思维观点上的自由主义。
他没有知青情结。他怜惜所有与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人,比如他的妹妹刘小茁。刘小茁15岁时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就塌了,万幸捡回一条命。后来为了照顾哥哥,妹妹放弃了回城,永远地扎根在河北保定,47岁提前“内退”。刘小萌给许多知青做的口述录音,都是妹妹帮助整理。刘小茁把这些说话南腔北调,声调忽高忽低的录音耐心地整理成文字,不为别的,就因为她也是“知青”。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已经三十余年,大规模的知青返城也早已结束于1979年,延续下来的仿佛是知青的宿命:大部分知青幸运地浮上了二元社会结构的上层,在城市找回了似乎本该如此的“天赋人权”;少数下乡知青扎根农村,结婚生子,成为了几乎永远无法摆脱身份的“乡下人”;回乡知青则理所当然地重复着他们祖祖辈辈的农民生活……
《炎黄春秋》主编吴思说,“知青容易把自己的经历神圣化”,虽然那是一段蹉跎了的青春。曾经的知青刘小佈说,“边缘化了的底层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那些长期默默地接纳和“再教育”了知青的农民……
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在中国那一代一千七百多万失学、失业的人群身上烙下了一个特殊的印迹——“知青”。倏忽之间,远去了几乎半个世纪,一部分知青已经不再敏感于旧事,另一部分知青,仍然容易被这根叫做“知青”的火索顷刻点燃。不管怎样看待这段往事,也许只有把它投射到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上,才能显示得更为清晰。
青春的记忆不该,也不会被遗忘,而且,应该记住的也不能只是知青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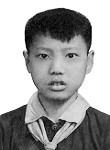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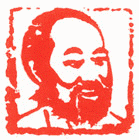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