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把远处卧牛般的山峦照得轮廓分明,水浮莲塘前那块晒谷坪早已扫得干干净净,风车和两张旧扮桶也被挪到弯角上去了,马灯便搁在一张沾满灰尘的台桌上,微弱的灯光一眨一眨地发出黄豆大的光亮。没有人去拧灯
芯,因为有了这月光。
板凳、木墩、还有摊开的半块晒簟上都坐了人。好久了,不知谁说了句:“小荣呢,小荣怎么没来?”弯弯塘基那边,就有一条人影披着月辉姗姗而至,是挟着二胡的小荣。有人让出一截板凳,小荣坐下来,理一理弓,再整一整琴弦,一曲熟悉的《良宵》便伴着轻灵的月光在禾坪上空低回跌宕。谁也不吱声,只有这胡琴声飘飘逸逸,追着潺潺的圳水,流向村外的小溪,流向大河,流向好远好远
的地方······
一年前的这一天,也是一个月色苍白的晚上,小村来了外乡客,一群长沙来的“学生奶崽”被大男细女围了一层又一层。不几天,大家便厮混得很熟了,白天,他们和村里人一起挖荒、薅草、翻凼肥,晚上,或是坐在破祠堂里开会学毛著;或是拎着手电筒去贫下中农家“结合”一阵子,日子就这么一天挨着一天过,
不知不觉间,竟流走了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
······塘基边又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一个男生忽地喊声“队长来了。”琴声戞
然而止。
队长光头赤膊,白色的扎头 裤裤头从腰带以上伸出老长一截。他将手里的竹篼烟杆点燃,不紧不慢地咂了两口。然后清清嗓子,习惯性地朝放马灯的台桌边走去。队长嗓门大 ,说一口地道的桃川官话,他充分肯定了“学生奶崽”一年来的进步,鼓励大家发狠干,要做扎根派,争取当先进到县里开代表会吃坨子肉。话不多,可寄望殷殷,博得一片掌声。接下来同学们便一个个表态,数小覃说得最好,又是念语录,又是谈心得,发誓赌咒要和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大家说完了,轮到小荣,只见他揉揉双眼,又扫一下禾坪里好几双慵困的眼睛,这才弓腰从地上拾起胡琴:“······眼皮子打架了,睡去吧,明日早起还得去 猫崽山挖红薯呢。”有人抬头一望,月儿不知何时已移到重重叠叠的远山后面,是不早了。四野里蛙鼓声声,凉风吹过,送过来几缕淡淡的桂花清香。于是大家就起身,有的拿着板凳,有的挟着蒲扇······这一年,小覃便常常去公社去县里开这号那号代表会,每日里穿鞋着袜。再没下过田,后来她终于熬成了脱产干部,远走高飞了,再后来,伙伴们也陆陆续续招工进了工厂。小荣却一直留在队里插
田扮禾挑粪桶。
日子过得好枯燥,月隐星淡的晚上,小荣便常常挟了二胡,一个人坐在禾坪里
悠悠地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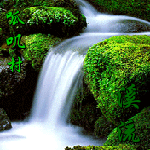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