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伯伯外传
(一)
骑摩托出外办事,对面街边一小老头,不就是单位以前的头头胡伯伯吗?
个子瘦小的胡伯伯两眼黯然无光,贴着靠第一小学围墙的人行道踽踽而行。本想与他对视时打声招呼,见他视身边的车辆与路人如无物,巳没有特意绕过去攀谈的必要——因为这是位与之恩怨一时拎不清的领导。
胡伯伯不过六十出头,退下来也就三、五年,并未到老朽之年。据说有些退下来的领导在位时前呼后拥,做人不凭脔心,用人“三分本事,七分人事”,单位里怨声载道,自是人走茶凉。也有退下来的领导抱怨世态炎凉,有些人虽是自己栽培过,在外面遇见如同路人。看多了这种“路人面孔”,对自己颐指气使的当年不堪回首,日子久了多会如胡伯伯一般行路,信不信由君。
胡伯伯以前可是集单位党政大权于一身,在主席台上两眼放光口若悬河作半天报告不歇气,跺一下脚单位都会地震的人物!
据说胡伯伯刚到任时穿一双老掉牙的三节头皮鞋下基层视察,那旧皮鞋脱线露出脚趾头,胡伯伯让女管理员拎到鞋摊去补。娇滴滴的女管理员捂着嘴对旁人抱怨,换谁也会把这快穿底的烂鞋扔了,还当个领导呢?真是个“胡伯伯”!
于是“胡伯伯”的外号在单位叫开了,他本姓符倒几乎被人忘了。
这“胡伯伯”外号还真有几分贴切:符的外形清瘦颇似巳故以越南北统一为己任的著名领袖胡伯伯,而艰苦朴素的形象也似国家不统一何以家为的胡伯伯。喜欢以长者自居的符倒也对人们送的“胡伯伯”之称欣然接受。
也有人说,月薪数千的胡伯伯寒酸的外表不过是清末《官场现形记》中穿破衣的杭州悭巡抚一样“表面作派”,他乱花起国家的银子眉毛都不会皱一下。
胡伯伯身边人曾透露,他从原单位到此上任时曾有个著名的“办公桌理论”:一个新领导上任,第一步就是要安排人改换机关各办公室布置,哪怕是把办公桌从左挪到右,也会显示出新领导权威及原领导恩泽的消逝。
光变动一下各办公室布置,把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花费毕竟有限,许多办公室还乘机争取些新办公用具。在“办公桌理论”指导下把各场馆花坛推倒重建,就真是“胡作非为”了!
胡伯伯说机关大院旗坛后的圆形大花坛与方形旗坛不匹配,硬是责成基建办把好好的圆形大花坛及几个小花坛推倒重建,全部改成菱形花坛。胡伯伯觉得“办公桌理论”光在机关推行还不够,又把下属几个单位馆所的花坛统一改成了他瞩意的菱形。
基建办老谭悄说,他这么一折腾,单位数十万银子就这么白扔了!
(二)
说来胡伯伯于我本有“知遇之恩”。八十年代刚兴起文凭热时单位大专以上文凭的人不多,不象后来不脱产的函授大专甚至硕士、博士文凭满天飞。胡伯伯也算“与时俱进”的人物,放言非大专以上文凭者不用。素昧平生的胡伯伯一个通知,把我从一个偏僻基层单位调机关负责企管办工作。据说他曾言,几个副职对我都有好评,“与其以后让别人提拔他,不如我送他个人情……”
为报“知遇之恩”,我与同事在短短两个月把单位的规章制度梳理了一遍,并重新修订了各项标准。上级企管部门对我单位这务虚的“标准化”工作予以认可,还表扬说,到底是学经济管理的,以前你单位XX来汇报工作可是一问三不知哟!后来我们草拟的部份标准还纳入了集团的标准系列。
正在我春风得意之际,无意中却犯下了机关工作人员之大忌。
当时单位领导班子都要安插一定比例“第三梯队”(年轻干部),有位中学学兄得以提拔为“三把手”。年初领导班子在某处秘密会议,好象是研究单位人事调整与一些重要事项。这学兄分管企管办等部门,要汇报企管办半年多工作却忘了拿我准备的材料,电话通知我赶紧再送一份复印件来小招会议室。我急忙骑车赶到两里外小招会议室,推开门就发现不合时宜——我是唯一来到领导秘密会议地点的普通干部。装作没看见胡伯伯脸上飞快掠过的一丝不快,把材料交给迎出门的“三把手”,飞快地离开了会场。
凭心而论,“三把手”待我不薄。几次评为单位先进,从基层调企管办,都有他暗中使劲。但从工作的角度看,“三把手”是遇到问题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城府很深的人,作为副职说不上是正职的好帮手。胡伯伯把老于世故,群众考评分在班子里最高,又处于第三梯队最佳年龄的“三把手”看作主要潜在对手。而我与“三把手”校友的关系,以及这次到秘密会场送材料一事,无疑加重了胡伯伯对我的猜疑(实则与“三把手”始终是工作关系)。
第三天我去胡伯伯办公室汇报一项工作,胡伯伯明显变了脸:“一个大学生,汇报工作还要看工作笔记?这怎么能提高管理水平!”我收起袖珍工作笔记本,草草收场走人。
又有一次,我无视胡伯伯的冷脸,去找“单位一枝笔”胡伯伯要一笔费用(费用开支由掌管人劳财的“一把手”批);胡伯伯冷冷地说,先去找XX(“三把手”)汇报,他分管你部门。实际上这钱上的事“三把手”根本作不了主……
突然想起,胡伯伯的冷漠可能还另有原因。
正月初二去岳父母家拜年,经过胡伯伯家小院,见本单位一些大小干部在胡伯伯家进进出出。不是年三十单位巳提前开过团拜会了吗?怎么还有这多人去胡伯伯家拜年?
刚好单位维修工厂的厂长迎面走来,见我看着他手上一对茅台酒(当然“给小孩的红包”是看不到),不好意思地说,“你在‘清水衙门’可以不来,我不能不来呀(维修工厂有不少外委项目)!”
以“清水衙门”自居,自以为靠干活不是靠走门子吃饭,我是少数未上门拜年的机关人员。但也有人说我,似乎忘了是胡伯伯把我从边远基层调到机关的!
胡伯伯初中未毕业从乡下参军,凭着他的精明能干从战士干到连副,转业后又从干事干到单位“一把手”,我并不认为他天生就是个不学无术一门心思算计别人的小人。他来单位后搞的一次别出心裁的干部理论考试就可看出他脑子的灵泛:不考当时流行的系统工程等机关干部死记呆背的现代化管理理论和时政,全考的是各基层单位电话号码与单位车牌号这些机关干部熟视无睹但工作中经常用到的东西,这些一时抄都无处抄的东西,还真把一些夹带理论与时政资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考试靠抄的机关老油子考砸了!竟有几位只考出二、三十来分……事后胡伯伯不无得意地说,当年他们在军区警卫连考核的项目之一就是记军区大院各单位的上百电话号和进出大院各单位数十车牌号,乃警卫战士基本功之一。
胡伯伯骨子里仍是个思想狭隘的山里老农。被广为传播的穿底三节头皮鞋故事,我相信不是他作秀,而是一个贫寒农家子弟的本色,尽管不排除此时他家钞票巳多得起霉。自己读书不多,他推崇读书人是真心。但多年官场的磨砺又使他多疑,对遇事绕着走的“三把手”诸多猜忌,一些误会又把我与“三把手”连到了一起……至于年节里某些领导家里送礼的人踏破门槛,巳不是领导是山里人或城里人出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大家巳深恶痛绝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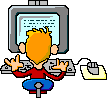



 湖南知青网
湖南知青网